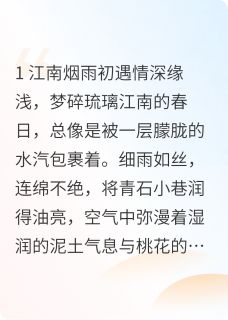《我听见了世界,也听见不爱你》小说简介
小编给大家带来主角是苏晚顾承屿林薇的小说,书名叫做《我听见了世界,也听见不爱你》,作者是最近人气很高的江越那的尔晴,小说讲述了:”他言简意赅,声音里听不出情绪,“这种场合,她不适合露面。你替她出席。”替她出席。四个字,像四根冰冷的钢针,瞬间贯穿了苏……
《我听见了世界,也听见不爱你》 我听见了世界,也听见不爱你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顾承屿收养我这个聋哑孤女,只因为我像极了他车祸昏迷的白月光。
>他教我模仿她跳舞、微笑,连房间都布置得和她一模一样。>三年后白月光苏醒,
他立刻送去价值千万的定制耳蜗:“薇薇需要最好的。”>而我攒了三年工资买的普通耳蜗,
终于让我听见了世界。>开机那天,他在阳台对助理说:“替身而已,让她签离婚协议。
”>火灾夜我拼命敲打消防铃,他抱着白月光冲出火场。>我蜷缩在火中时,
看见他书桌抽屉里我的照片——背面写着“赝品”。>遗书只有一行字:“世界很吵,
但安静死去也好。”---冰冷的仪器贴附在耳后崭新的皮肤上,
带着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硬度。苏晚坐在医院纯白的椅子上,
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棉质裙摆的边缘,呼吸轻得如同蝶翼震颤。
医生调试设备的手指在她余光里晃动,像隔着毛玻璃看水中的鱼影。她全部的感官,
都死死钉在右耳后方那一小块被植入不久的、冰凉的金属上——那是她三年积蓄换来的门,
一扇她赌上所有卑微积蓄,妄想能推开另一个世界的门。忽然,
一阵尖锐的蜂鸣毫无预兆地刺入混沌!她猛地一颤,像被无形的针扎中脊椎,
整个人弹了一下。那声音粗暴、陌生、带着金属的刮擦感,
瞬间淹没了她二十年来早已习惯的、无边无际的寂静牢笼。不是想象中溪流的潺潺,
不是鸟儿的清鸣,是无数根生锈的钢针在刮擦玻璃。她下意识地捂住双耳,
可那尖锐的噪音并非来自外界,而是从她自己的颅骨深处,蛮横地钻出来。
医生似乎说了什么,嘴唇开合。苏晚茫然地抬头,视线艰难地聚焦在他不断翕动的唇上。
世界在她眼前扭曲变形,只剩下那两片快速开合的唇瓣,像两条挣扎的鱼。
她读唇语的能力在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噪音里完全失灵了。
“……正常……适应……”几个破碎的音节勉强拼凑出来。她僵硬地点点头,
心脏在胸腔里失重般狂跳。这就是声音?这就是她抛弃所有安全感,
像扑火的飞蛾一样追逐的世界?一片令人心悸的、冰冷的、充斥着金属噪音的荒原?
她闭上眼,试图在那片令人窒息的蜂鸣汪洋里寻找一个支点。意识在混乱的声浪中沉浮,
像一叶随时会被撕碎的扁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漫长如一个世纪。
在一片混沌的嗡鸣与刺耳的刮擦声中,一个低沉、微带磁性的声线,
如同沉船中浮起的唯一一块木板,异常清晰地穿透了厚重的噪音壁垒,
抵达了她混乱的感知核心。“……好了吗?”是顾承屿的声音。苏晚猛地睁开眼,
像溺水者骤然吸到氧气。那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瞬间在她耳中那一片嘈杂的废墟上,
开辟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周围的蜂鸣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推开了几寸,为他让出了空间。
她急切地循声望去。顾承屿就站在几步之外,背对着明亮的窗户。
高大的身影被逆光勾勒出一道略显冷硬的轮廓。他并没有看她,
目光落在医生手中的平板电脑上,侧脸线条流畅却没什么温度,
眉宇间似乎习惯性地笼着一层不易察觉的、审视般的疏离。可他的声音,
刚才那简单的三个字,却像带着温度的光,精准地落进她一片狼藉的听觉世界。
苏晚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连指尖都微微蜷缩起来。
她努力地、贪婪地捕捉着空气中属于他声音的微弱震动。
原来……原来顾承屿的声音是这样的。比她无数次在寂静中用指尖描摹他唇形时想象出来的,
更沉,更稳,像某种质地厚重的丝绒,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感。
她甚至能分辨出他声带震动时那一点点微妙的颗粒感。一种近乎眩晕的狂喜攫住了她。
她甚至忽略了耳中依旧顽固存在的其他噪音。这扇门,真的打开了。她听见了!
第一个真正听见的、属于这个真实世界的声音,是顾承屿的。她望着他,
嘴角无法控制地向上弯起,一个纯粹到近乎傻气的笑容在她苍白的脸上绽开。她想告诉他,
她听见了!听见他的声音了!这声音如此真实,如此清晰!不再是臆想,
不再是纸上苍白的唇语!她想冲过去,笨拙地、激动地用手语比划给他看。然而,
就在她身体微微前倾,几乎要做出手势的瞬间——顾承屿的目光,终于从平板上移开,
落到了她脸上。那眼神里没有她期待的丝毫动容,没有一丝好奇,甚至连基本的询问都没有。
只有一种极淡的、例行公事般的审视,像评估一件物品是否完好无损。
那目光扫过她脸上尚未褪去的惊喜笑容,如同冷水浇过炭火,只留下刺啦一声无形的轻响,
和迅速弥漫开的寒意。他微微蹙了下眉,那动作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
却带着一种明确的否定意味。然后,他冷淡地移开了视线,
仿佛她脸上那不合时宜的笑容是一种需要被纠正的失态。苏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如同骤然冻结的湖面。那股刚刚涌起的、几乎要冲破胸腔的热流,
被这冰冷的一瞥生生冻结、压回深渊。她像被施了定身咒,
所有想要表达的冲动都凝固在指尖。刚刚被声音点亮的那个世界,
仿佛又迅速蒙上了一层灰暗的纱。她默默地收回目光,低下头,
视线落在自己放在膝盖上、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的手上。那双手,
曾无数次模仿另一个女人的动作,在空旷的房间里,对着巨大的落地镜,
笨拙地旋转、伸展、微笑。为了模仿林薇,那个沉睡在顾承屿心底的女人。
顾承屿带她离开孤儿院的那天,雨水冰冷。他高大的身影站在破败的走廊尽头,
昂贵的皮鞋踩在潮湿的水磨石地面上,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落在她脸上,审视了很久很久。
久到她以为自己要被那目光灼穿。最终,他微微颔首,对旁边的助理说了句什么。
她只看到助理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任何声音。那一刻,她只是本能地感到一种冰冷的恐惧,
如同被蛇盯住的鸟。后来她才知道,他带走她,只因为她这张脸,
像极了车祸昏迷、沉睡不醒的林薇。像得惊人,像得残忍。“她叫林薇。薇薇。
”顾承屿曾递给她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容明媚,眼神灵动,穿着洁白的芭蕾舞裙,
像一只随时会振翅飞走的白天鹅。他让她学。学林薇走路时轻盈的步态,
学她笑起来时眼角弯起的弧度,
学她说话时(他要求她练习读唇语)那种温柔又带点娇俏的神态。甚至,连她的房间,
也被布置成了林薇房间的样子——浅蓝色的墙壁,巨大的落地镜,
窗边一架蒙尘的白色三角钢琴,
床头柜上永远摆放着一束新鲜的白玫瑰(那是林薇最爱的花),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名为“雨后晨曦”的冷冽香水味。这里是林薇的囚笼,而她,苏晚,
是囚笼里一个被精心打磨的、无声的影子。她存在的全部意义,
就是在这座巨大的、无声的坟墓里,模仿一个沉睡的灵魂。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顾承屿让人送来的芭蕾舞裙,站在那面巨大的落地镜前。镜子里的人,
穿着不属于自己的华服,身体僵硬得像一具提线木偶。顾承屿就坐在她身后的沙发上,
目光沉沉地落在镜中的倒影上,仿佛在透过她,拼凑另一个人的轮廓。
他无声地用手语命令:“踮脚。转圈。”手势简洁,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她笨拙地抬起脚,
身体摇晃,重心不稳,重重地摔倒在地毯上。膝盖磕得生疼,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她抬起头,
望向顾承屿,带着一丝本能的求助和委屈。然而,回应她的,是他眼中瞬间凝结的冰霜,
和唇边那抹毫不掩饰的失望与厌恶。他甚至没有起身,只是冷冷地用手语比划:“起来。
继续。别哭哭啼啼,薇薇从不这样。”那一刻,地上的凉意顺着膝盖,一路冰封到了心脏。
她明白了,在这里,眼泪是廉价的,脆弱是多余的。她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像”。
像一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赝品。“苏**,顾总的意思是,您需要尽快适应这个状态。
”医生调试着平板,声音恢复了公事公办的平稳,
将苏晚从冰冷的回忆里拽回同样冰冷的现实。她点点头,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耳后那片区域,
努力在持续的、令人烦躁的嗡鸣和失真中,捕捉医生话语的碎片。
每一个字都像蒙着水汽的玻璃,模糊不清,需要耗费极大的心力去辨认。
“……初期……杂音……正常……坚持训练……”她用力点头,表示理解。眼角的余光,
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几步之外。顾承屿已经接起了电话,他侧着身,对着手机,
线条冷硬的侧脸似乎柔和了一丝。“嗯,刚结束。”他的声音不高,
但穿透了诊室里的仪器低鸣,清晰地钻入苏晚刚刚开启的听觉世界。那语调,
是她从未感受过的温柔,像冬日里陡然照进的一缕暖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
“……耳蜗?订了,德国那款顶配,声场模拟最接近自然的那套。”他停顿了一下,
似乎在听对方说话,然后低低地笑了声,那笑声像羽毛拂过心尖,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宠溺,
“傻瓜,当然要给你最好的。钱不重要,只要你能听见。”苏晚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
她猛地低下头,视线死死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帆布鞋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柔软的肉里。
德国顶配。声场模拟最接近自然。钱不重要,只要你能听见。每一个词,
都像一把烧红的钝刀,反复地、狠狠地捅进她的心脏,再带着血肉模糊的温度残忍地搅动。
她耳后这枚廉价人工耳蜗带来的尖锐不适,此刻显得如此可笑而卑微。
原来声音也有三六九等。原来顾承屿的温柔,从来不是吝啬,只是从不属于她。
一股浓烈的、带着铁锈味的腥甜猛地涌上喉咙,又被她死死咽了回去。她想起自己这三年。
顾承屿给她的生活费,维持着一种体面却绝不算宽裕的水准。她像仓鼠一样,
一点点地积攒着每一分钱。不敢买新衣,不敢添置任何非必需品,甚至为了省下交通费,
在偌大的别墅区里,顶着烈日或寒风,步行几公里去最近的超市买打折的日用品。
无数个深夜,她对着镜子练习林薇的微笑,对着空气练习林薇说话的唇形,
只为了换取他一丝满意的眼神,或者,仅仅是不再被那冰冷失望的目光刺伤。
她以为那枚耳蜗,是她通往他世界的最后一张船票,是她摆脱这无声囚笼的唯一希望。
现在她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聋哑的赝品,在做着一场无声又自取其辱的梦。林薇醒了,
正主归来,她这个拙劣的模仿者,连拥有廉价声音的资格,都成了原罪。“苏**?
”医生提高了音量,带着一丝询问。苏晚猛地回过神,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
她慌乱地抬手去擦,动作粗鲁,指关节蹭得脸颊生疼。
“对不起……我……”她试图开口解释,刚获得的声音系统却像生锈的齿轮,
发出几个干涩、扭曲的音节,难听得让她自己都心惊。她立刻闭上嘴,
绝望地用手语比划:“抱歉,有些不适应。”医生理解地点点头。顾承屿也结束了通话,
他收起手机,目光淡淡地扫过苏晚布满泪痕的脸,眉头再次蹙起,那里面没有心疼,
只有一种被打扰的不耐烦。“哭什么?”他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冷硬,像冰凌敲击,
“吵死了。走了。”他说完,不再看她,转身径直朝诊室外走去,步履沉稳,没有丝毫停顿。
那高大挺拔的背影,隔绝了诊室惨白的光线,在她模糊的泪眼中,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冰山。
苏晚的身体晃了晃,几乎要支撑不住。医生似乎想扶她,她猛地摇头,用尽全身力气站稳,
胡乱地用手背擦掉脸上的泪水,跌跌撞撞地跟了上去。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烙铁上,
耳中那廉价耳蜗传来的、顾承屿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一下,一下,
沉重地碾过她刚刚被碾碎的心。车子无声地滑入顾家别墅的车库。深灰色的金属门缓缓落下,
隔绝了外面午后过于明亮的光线,也将苏晚重新投入这座巨大而熟悉的囚笼。空气里,
“雨后晨曦”的冷香一如既往地弥漫着,像一层无形的膜,包裹着所有属于林薇的痕迹,
也包裹着她这个赝品的窒息感。顾承屿解开安全带,动作利落,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径直推门下车。苏晚默默地跟着,脚步虚浮。车库的感应灯随着他们的脚步一盏盏亮起,
又在一段距离后无声熄灭,光影在她苍白的脸上明明灭灭。穿过连接车库与主宅的走廊,
步入空旷得能听见自己心跳声的客厅。顾承屿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
朝着二楼书房的方向走去。苏晚习惯性地停下,准备回到自己那个“林薇的房间”。“苏晚。
”顾承屿的声音突然在楼梯转角响起,不高,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穿透力,
清晰地刺入她耳中。她身体一僵,下意识地抬起头望向他。逆着二楼走廊投下的光线,
他站在楼梯上方的阴影里,面容有些模糊,只有那锐利的视线,如同实质般落在她身上。
“今晚有个慈善晚宴,”他的语气平淡无波,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你准备一下,跟我去。”苏晚愣住了。慈善晚宴?他从未带她出席过任何公开场合。
她只是他藏在金屋里的影子,一个不能见光、不能发声的替代品。
巨大的困惑和一丝荒谬的不安瞬间攫住了她。她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
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慌乱地用手语比划:“我?为什么?”动作因为急切而显得凌乱。
顾承屿的目光扫过她飞舞的手势,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似乎对她这种“原始”的表达方式感到一丝不耐。“薇薇刚醒,身体还很虚弱,需要静养。
”他言简意赅,声音里听不出情绪,“这种场合,她不适合露面。你替她出席。
”替她出席。四个字,像四根冰冷的钢针,瞬间贯穿了苏晚的心脏,
将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钉死在耻辱柱上。原来如此。正主需要休养,
所以赝品被推上舞台,继续扮演那个完美的“林薇”。多么讽刺,多么顺理成章。
一股冰冷的麻木感从脚底迅速蔓延至全身,冻结了血液,也冻结了所有的挣扎和痛感。
她垂下眼睑,不再试图表达任何疑问或抗拒,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动作僵硬得如同坏掉的木偶。顾承屿似乎对她的“识相”很满意,不再多言,
转身消失在二楼走廊的阴影里。沉重的晚礼服像一层华丽的枷锁,勒得苏晚几乎喘不过气。
深蓝色的丝绒长裙,缀着细碎的仿水晶,在宴会厅璀璨夺目的水晶吊灯下折射出冰冷的光泽。
裙摆很长,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提着,才能避免绊倒。这裙子的款式,甚至颜色,
都和林薇某次在社交杂志上刊登的照片惊人地相似。苏晚僵硬地挽着顾承屿的手臂,
感觉自己的每一寸肌肉都绷紧到了极限。宴会厅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空气里混合着昂贵的香水、雪茄和食物的气味,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甜腻。
无数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带着探究、好奇和毫不掩饰的惊艳。
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在她脸上逡巡,窃窃私语像无形的潮水般涌来。
“顾总身边这位……以前没见过啊?”“长得……真像林**!”“气质差了点吧?
林薇可是跳芭蕾的,那身段……”“嘘……听说林薇醒了?”这些声音,
透过她耳后那枚廉价的耳蜗,失真地传入耳中,带着嗡嗡的回响和金属的质感,
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持续不断地扎着她的神经。
她努力维持着脸上模仿来的、属于林薇的那种温婉得体的微笑,唇角上扬的弧度精确到毫厘,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笑容的肌肉早已僵硬酸痛。顾承屿侧过头,嘴唇靠近她的耳廓。
他温热的呼吸拂过她的皮肤,带来一阵细微的颤栗。然而,
他的话语却冰冷得像手术刀:“笑自然点。薇薇笑起来,眼睛是弯的,像月牙,
不是你现在这样,像个假人。”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她能听见,
带着毫不留情的指令和挑剔。苏晚的心猛地一沉,一股尖锐的羞耻感直冲头顶。
她下意识地想让自己的眼睛弯起来,努力调动着眼周的肌肉,
却只感到一阵徒劳的僵硬和酸涩。她不是林薇,
小说《我听见了世界,也听见不爱你》 我听见了世界,也听见不爱你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