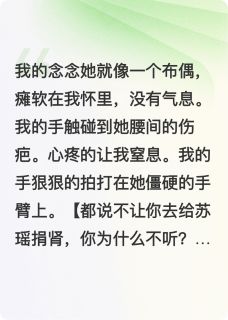《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小说简介
《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完全让读者入戏,不管是江哲秦岚秦诺的人物刻画,还是其他配角的出现都很精彩,每一章都很打动人,让人能够深入看进去,《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所讲的是:”秦岚笑了。一声真实的、柔和的、没有剧本的笑。“那么糟糕,嗯?”江念笑了:“没人一开始就在正确的杯子里,但大多数人不会去……。
《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 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她又来了。秦岚的声音毫无波澜,高跟鞋敲击光洁大理石地面的声音,
像是某种警告:“如果你没准备好迎接答案,就不要问。”旁边的林助理没敢问。
秦岚只是拐过一个弯,脚下的定制高跟鞋踏在玻璃幕墙走廊的地毯上,悄无声息,
直到那片混乱的全貌彻底展现在眼前。安全玻璃的碎片如冰雪般散落一地。
两个行政助理吓得呆若木鸡。而六岁的秦诺,正赤着脚,像一个桀骜不驯的女王,
站在一片狼藉中央。她呼吸急促,双眼死死盯着前方。在房间的另一端,
她的双胞胎妹妹秦默,蜷缩在角落,身边是她被撕破的布偶熊,一动不动,眼神空洞,
仿佛灵魂早已飘向远方。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如幽灵般出现。
一个穿着浅蓝色保洁制服的男人,从员工电梯里走了出来,袖子卷到手肘,
拖把桶在他身后安静地滚动。他没说话,也没退缩,只是平静地扫视着全场:两个孩子,
一场公司危机,一地碎成齑粉的玻璃。然后,他从容地走向那片狼藉。“站住。
”秦诺警告道,声音嘶哑,“我就要它碎着。”男人没有停步。
秦诺从地上抓起一块锋利的玻璃片,像握着一把匕首。“我说了,别管它!
”林助理本能地想上前,秦岚却伸出一只手:“等等。”男人在离秦诺不到一米的地方蹲下,
将一样小而柔软的东西放在地上。那是一张从行政茶水间拿来的餐巾,
上面用墨水写着一行清秀的字:破碎之物,亦待温柔。秦诺眨了眨眼。然后,
男人慢慢放下了一双崭新的拖鞋,粉色的,软绵绵的,看起来像是从二手店淘来的。接着,
他开始用自己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去清扫玻璃的边缘,
任凭一道细细的血痕在他拇指上慢慢形成。“他疯了?”林助理倒吸一口凉气,
“这等着吃官司呢!”但秦岚没有回答。她正看着秦诺。秦诺开始哭了,不是嚎啕大哭,
只是一滴无声的眼泪,安静地滑过她倔强的脸颊。她的手指松开了,
玻璃碎片“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那双粉色的拖鞋,还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无人触碰。
男人没有看她,没有赞美,也没有怜悯。他只是打扫。不知为何,那份沉默,
胜过了千言万语。后来,在顶层那间寂静无声的总裁办公室里,
秦岚手里反复摩挲着那张餐巾纸。“她的情况在恶化,”林助理站在落地窗边,语气沉重,
“两周内第三次了。您请来的专家一个接一个地被气走,董事会又在催秦默**的入学问题。
”“自从我先生去世,她就没再说过话。”秦岚喃喃道。“我知道。”“秦诺心里全是火,
而秦默……”秦岚的声音顿住了,
不是因为情绪——她不允许自己流露情绪——而是因为深入骨髓的疲惫,
“她正在一点点消失。”林助理的目光落在那张餐巾纸上:“您认识那位保洁员吗?
”“不认识。需要我去查一下吗?”秦岚犹豫了片刻:“不,先观察一下。暂时。
”林助理挑了挑眉:“您是想把您千金的情绪稳定,寄托在一个拿拖把的男人身上?
”“我不信任何人,”秦岚说,“但这是几个月来,秦诺第一次……是主动放下,
而不是砸向什么。她松手了。”林助理沉默了,
半晌才干巴巴地说:“那我先把下一位儿童心理专家的预约推迟。”与此同时,
在行政层下的后勤通道里,江哲在一盏忽明忽暗的灯下冲洗着拇指上的伤口。
他十岁的女儿江念,坐在旁边的工具箱上,速写本平放在膝盖。“那个小姑娘,心里很愤怒。
”江念轻声说。“她有权利愤怒。”江哲一边擦干手一边回答。“你没有冲她发火。
”“发火,是说给那些以为自己会被倾听的人听的。”江念抬起头:“你觉得,
她看见那张餐巾纸了吗?”“我想,”江哲说,“她一直在等一个,
不会因为她的尖刺而移开目光的人。”江念的画笔停住了。“她会吓跑别人的,爸爸。
”“她也吓坏了她自己。”江念把她的画转过来。画上,一个愤怒的赤脚女孩,
站在一场玻璃碎片的风暴中,双手却无力地张开,眼神里满是哀求。“她不坏,
”江念轻声说,“她只是心里太吵了。”江哲笑了:“这比我听过的所有专家诊断都好。
”第二天早上七点,秦岚走进中庭咖啡厅,发现秦默已经在了,坐在昨天那张长凳上,
身边放着一瓶没动的热牛奶。秦诺双臂交叉靠在墙上,像个小哨兵。而江哲就坐在不远处,
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他从一个掉漆的保温杯里倒着自己的热茶,
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旧书。他没和女孩们说话,只是安静地待着,
好像他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也许,秦岚想,他确实是。她走上前:“江先生。”他抬起头。
“你是这里的保洁员。”她确认道。他慢慢站起身:“是的,秦总。”“你昨天违反了规定。
”他没有辩解。她双臂交叉,“这不是训斥,只是陈述。”他依旧沉默。“我能问问,
”她继续道,“你为什么写那句话吗?
”他只眨了一下眼:“因为破碎的孩子需要的不是修复。他们需要的是一个,
懂得如何捧起那些碎片,而又不伤到自己的人。”秦岚凝视着他。在漫长的,
超乎任何人预料的寂静里,唯一的声响,是秦默在旁边,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
秦默第一次微笑的时候,没人看见。那是在西走廊,一扇她过去常常忽略的窗户旁。
光线从那里倾斜地洒在光洁的地板上,温暖而柔软,像是来自她几乎记不得的童年。
那天早上,江念在那里放了点东西。一个倒扣的旧画板,
上面整齐地排着四根粉笔:蓝、黄、白、红。没有言语,没有指示,只有可能性。
当秦默走过时,走廊已经空了,但那些颜色留了下来。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跪下,
拿起白色的那支,开始画。一个圆圈,一个太阳,一扇门。她还不确定那是什么。
然后江念悄悄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小杯果汁和一块用纸巾包着的饼干。她坐在她旁边,
不远不近。秦默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江念只是拿起了红色的粉笔,开始在秦默的太阳旁边,
画上了自己的太阳。“谁允许的?”林助理从运营夹层的玻璃墙后窥视着,压低声音问。
秦岚没有回答。现在是早上八点多。她的双胞胎女儿,在华宇集团的地盘上,
像两个从未失去父亲、从未逼疯一排心理专家的普通孩子一样,在地板上画画。
但这一次的沉默,不再是尖锐的、暴力的。它是完整的,专注的。“我没有允许,
”秦岚终于说,“但我也不打算阻止。”“她们是孩子,秦总,”林助理说,“不是实验品。
”“不,”秦岚喃喃道,“她们是游魂,而终于有人,为她们推开了门。”第二天早上,
粉笔画不见了。不是被擦掉,而是被保存了下来。江哲拍了照片,彩印出来,
放进小小的塑料相框里,留在了女孩们在咖啡厅常坐的椅子下面。秦诺嗤之以鼻:“真行,
现在连地上的涂鸦都要裱起来了。”江念没有退缩:“我爸爸说,能让孩子笑出来的东西,
就是艺术。”秦诺翻了个白眼:“听起来你爸没见过真正的艺术评论家。”“是没有,
”江念温和地说,“但他对自己,一直是个最严苛的评论家。”秦诺眨了眨眼,这句话,
触动了她心里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江哲双臂交叉地站在走廊里看着,拖把被遗忘了。
不是疏忽,而是因为这一次,这栋大楼里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立刻被清理。他看到了变化,
感受到了。不大,不响亮,但稳定,像水滴石穿。
秦岚不请自来地站到他身边:“你在破坏结构。”“我不是在建立结构,”他回答,
“我是在结构里,为她们腾出呼吸的空间。”“你没受过处理选择性缄默症的训练。
”“我没想让她开口说话,”江哲说,“我只是想让这里足够安全,
安全到如果她某天想说了,她会相信,这世上还有人在听。
”秦岚看着他:“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做?”江哲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因为曾经有个人,在我最不值得的时候,倾听了我。
那改变了一切。”她没有再问,但她留了下来。那天下午,
休息室的公告板上出现了一张新的日程表:“7:30走廊艺术时光”,
“8:15与江念的安静早餐”,“9:00与江叔叔的清洁游戏”。没人签名批准,
但有人用公司的官方信纸打印了它。江念注意到了角落里的首字母缩写。“LX,
”她对父亲耳语道,“林溪。”江哲笑了:“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掌管着总裁日程表的女人。
”那周晚些时候,秦诺又爆发了。这次是在公司电梯里。人太多,声音太吵。
楼层提示音让她想起了医院里仪器的蜂鸣声。她尖叫着,踢打着电梯内壁,
按下了紧急停止键。秦默立刻缩进了壳里,蜷缩在墙角,双眼圆睁,手指死死地抠着袖子。
江哲第一个赶到,但他没有进去。他只是蹲在敞开的电梯门外。江念盘腿坐在他旁边,
手里拿着一个她两年没碰过的布偶熊。秦诺怒视着:“不准进来!”江哲点点头:“好。
”“那你待在这儿干嘛?”“为了靠近,”他说,“靠近,不等于闯入。”这句话,
如晨钟暮鼓,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慢慢地,秦诺瘫倒在地板上,不是投降,
只是终于卸下了力气。江念小声问:“我能把这个滑给你吗?”秦诺没回答。
江念还是把熊滑过了电呈的门槛。它轻轻碰到了秦诺的脚。她盯着它看了很久很久。然后,
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她低语道:“它叫小安。”江哲的呼吸一滞。躲在走廊尽头的秦岚,
靠在墙上,用手捂住了嘴。那天晚上,在那个被改造成储物休息室的保洁间里,
江哲和江念坐在一只牛奶箱上。她正在把她的粉笔画描摹到一个笔记本里。“她记起来了,
”江念轻声说,“她只是害怕,如果说出来,会再次忘记。”江哲点点头。
“她今天叫你江叔叔了。”江念补充道。“是吗?”他笑了。“不是讽刺的那种。
”江克笑了:“那问题可就严重了。”江念停顿了一下:“你觉得她会好起来吗?
”他想了想,然后说:“我不认为她需要‘好起来’。我认为她需要相信她‘可以’好起来。
”江念歪了歪头:“那秦默呢?“江哲的目光柔和下来:“秦默已经在说话了。
”江念皱起了眉:“可她什么都没说啊。”“她在说,”江哲说,
“用她唯一信任的语言在说。”江念合上笔记本,靠在他的肩膀上:“那我希望,
”她低语道,“终于有人能听懂她。”回到楼上她的办公室,
秦岚在桌上发现了一张揉皱的纸条,没有信封,只是折叠着。
她打开它:即使是最安静的孩子,也在呐喊。如果你听不见,也许是时候,
学习一种新的倾听方式了。——江念秦岚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关掉电脑,走出办公室,
站到秦默第一次微笑的那扇粉笔画窗前。多年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像个总裁,
而像个母亲。江哲第一次没有问任何问题的时候,秦默留了下来。
那是在一间被遗忘的办公室里,
江哲把它温柔地改造成了一个为女孩们准备的、灯光柔和的角落。一个豆袋沙发,
几叠彩色卡片,一盏只需触摸就能点亮的台灯,还有一个安静的男人,拖把靠在门边。
秦默盘腿坐在地毯上,背对着他画画。江哲没有问画的是什么,没问她感觉如何,
也没问秦诺为什么迟到。他只是坐着,等着。那是一切的开始。“你在浪费时间。”第二天,
秦诺直言不讳地说。她双臂交叉地靠在门框上,
打量着像一棵树一样耐心地待在房间里的江哲。“她那样的人不说话。除非你拿好处收买她。
”江哲没有动。“你试过和她一起,安安静静地待着吗?
”秦诺眯起了眼:“我跟她住在一起。那不叫安静。”“不,”江哲轻声说,“那叫生存。
”秦诺歪了歪头:“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你不是医生,不是治疗师,你就是个通下水道的。
”“有时候,”江哲说,“了解一个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坐在他们留下的烂摊子旁边,
并且不逃跑。”秦诺盯着他,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然后转身走开了。但那天晚上,
她在“安静房间”外留下了一张揉皱的餐巾纸。铅笔潦草地写着几个字:她梦见红色。
江念第一个注意到了。“她开始打开她心里的门缝了。”她告诉父亲。在本子上,
她画了一个蜷缩在暴风云里的小女孩,手里却紧紧抓着一个红色的气球。
“你觉得她梦里有颜色吗?”江哲问。“我觉得她在颜色里躲藏,”江念回答,
“红色是她的愤怒,黄色是她的妈妈,蓝色,”江念犹豫了一下,“是秦诺。而白色,
”她说,“是当再也没有人问你‘还好吗’之后,剩下的颜色。”江克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白色的墙壁,医院的病房,一个三个月没说话的小女孩,最后低声说:“告诉她,
对不起,我没能及时醒来。”他把那些话告诉了她的母亲。但那个女孩再也没有说过话,
而江哲也再没有治疗过任何病人。直到现在。那周晚些时候,
在九楼和十楼之间的消防通道里,秦默的速写本掉了。书页散落一地。秦诺捡起来,
停在一幅她以前没见过的画上。三个简笔画小人,一个长发的是妈妈,一个卷发的是她自己,
一个扎着小辫子、穿着红衣服的是秦默。她们都牵着一个高个子、头发有点乱的人。
旁边还有一辆保洁推车。秦诺皱起了眉:“这是……江叔叔?”秦默没有回答,
只是拿出一支红色的蜡笔,圈住了那个人的手。不是他的脸,不是他的微笑,只是那只手。
它说明了一切。那天晚上,秦岚发现自己正凝视着办公室的窗户,
而林助理则在汇报她的会议日程。“您没在听。”林助理说。“我在听。”“不,
您在想事情。”秦岚转过身:“她们信任他,比信任我更多。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刺眼?
”林助理长久地看着她:“她们不是更信任他,秦总。她们信任的,是他在她们身边时,
变成的那个人。”“那我在她们身边是什么样的?”林助理停顿了一下:“一个仍然害怕,
会再次打碎已经破碎的东西的母亲。”接下来的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响亮。第二天早上,
江哲在储物柜上发现了一张便利贴,是秦诺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的:她不需要英雄。
她需要一个,在她哭泣时,不会退缩的人。下面是一个小磁铁,
一个破碎的玩具人偶被重新粘好了。当他拿给江念看时,她笑了:“你正在走进她的心里。
”“我不想走进她心里,”江哲说,“我想陪她走一段路。”到周末,一种新的仪式出现了。
江念会带着秦默和秦诺进入安静房间。没有言语,没有指示,只有颜色。
江哲会拿着一托盘回收的文件夹等着,
每个文件夹上都标着一个问题:“今天什么让你觉得沉重?”“如果你的情绪有天气预报,
会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种你希望消失的声音?”秦默从不大声回答,
但她会画画、圈点、做手势。有时候她会在地板上放一件小东西——一枚硬币,一个回形针,
一根线。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都在说:“我仍在这里。”一天下午,
秦岚双臂交叉地站在那个房间外。
看着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她已经快不认识的女孩——在没有尖叫、没有退缩的情况下互动。
她转向江哲:“你做这些,却不向她们索取任何东西。”他点点头。“我不懂。
”江哲看着她,眼神友善但坚定:“有时候,治愈不是来自修复,它来自被见证。
”“如果我不知道如何见证呢?”“那就从事情变得不舒服时,不转身走开开始。
”秦岚眨了眨眼。她没意识到自己曾走开过多少次。第二天,
秦诺把自己的椅子搬进了安静房间,坐在江哲旁边,一言不发,
但她递给他一张纸条:“你觉得,破碎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好好的大人吗?
”他回写道:“只有那些,被允许在平静中破碎的孩子,才会。”那天晚上,
秦岚打开她的私人邮箱,
开始给董事会写一封邮件:“我不会将江哲先生从他目前的职责中调离。
他不是持证的治疗师,但他比那更好。他是一个无需询问便能理解的人,而眼下,
这正是我女儿们最需要的。”她点击了发送,几个月来第一次,她一觉睡到了天亮。
门打开时没有吱呀作响,它只是叹了口气,仿佛也一直在等待呼吸。714房间。
曾经是存放闲置横幅和破损椅子的储藏室,
现在散发着淡淡的柑橘清洁剂和薰衣草精油的香气。
一串柔和的球形灯像安静的星星一样悬挂在天花板上。一张旧货店的地毯温暖了冰冷的瓷砖。
一个褪色的豆袋沙发放在角落里,像一个无需回应的邀请。而在这一切的中心,
一块小白板上写着:“这是一个,无需解释任何事情的房间。”秦默第一个进去。
她没有犹豫。她只是走进去,坐在地毯上,开始画画。“她走起路来,
好像已经知道这个空间是她的了。”林助理在观察玻璃后面小声说。秦岚站在她旁边,
沉默地看着她的女儿们,一个安静,一个像盘绕的弹簧,
多年来第一次毫无恐惧地待在一个房间里。“她甚至没看我一眼。”秦岚声音遥远地说。
“那不是拒绝,”林助理回答,“那是信任。她知道你会留下。
”秦岚眨了眨眼:“我什么也没说。”“你不需要说。”林助理转向她,
“当你停止试图修复她们的沉默时,你就为她们留出了用自己的方式填补它的空间。
”秦诺在门口徘徊,不确定。江念已经坐在地板上,把彩纸折成小星星。她没有抬头。
“我不做手工。”秦诺咕哝道。“很好,”江念平静地说,“这些不是用来做的。
它们是用来记住的。”秦诺皱起了眉:“记住什么?”“我们幸存下来的事,”江念回答,
一边把一颗折好的星星滑过地毯,“每一颗都是一个记忆。不全是好的,但都是我们的。
”江哲坐在窗边,修理一个坏掉的风铃,它的木制部件在他指尖下轻轻旋转。
“记忆不是用来忘记的,”他说,“它们是用来建造新东西的。”那天下午,
秦默在角落的架子上放了一块小石头。它有一个锯齿状的边缘,
一条粉色的丝带松松地系在上面。一直安静地站在门口的秦岚问:“那是什么?
”江哲轻声回答:“一个占位符。”“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她还没准备好讲述的故事。
”秦岚慢慢地跪在女儿旁边:“这跟爸爸有关吗?”秦默没有抬头,
但她握着丝带的手收紧了。“她不必说是的。”江哲温和地说。
秦岚转向他:“而我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吗?”江哲看着她:“你应该在场见证它。
”那天晚上,秦诺自己回到了714房间。没有日程安排,没有理由。她发现江哲独自坐着,
那个风铃现在挂在他上方,修好了,它的木制小鸟在懒洋洋地转圈。“你总是坐在沉默里。
”她问。“我坐在,感觉安全的地方。”他回答。
秦诺把她的包扔到地板上:“人们认为我很愤怒。”“你是吗?”“有时候。
”江哲点点头:“那很公平。”“但有时候,”她补充道,声音变小了,“我只是不想消失。
”江哲转向她:“你没有在消失,秦诺。你在标记空间。”她皱起了眉:“有什么区别?
”“消失,是当人们不再看见你。标记空间,是当你终于在无需大喊的情况下,被看见。
”秦诺坐在他旁边。没有更多的问题。第二天早上,女孩们来得很早。
窗台上放着两个马克杯。一个标着“仅限大人”,另一个标着“倾听的大人”。
秦岚看到它们时停顿了一下:“我是哪个?”她问。江念递给她第三个杯子:“还在学习中。
”秦岚笑了。一声真实的、柔和的、没有剧本的笑。“那么糟糕,嗯?
”江念笑了:“没人一开始就在正确的杯子里,但大多数人不会去尝试第三个。
”秦岚双手接过它,像是捧着什么脆弱而温暖的东西。秦默开始画家庭。不是她的,
不完全是,但很接近。一幅画里有四个人物排成一行。一个穿着高跟鞋的高个子女人,
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卷发女孩,一个拿着气球的小女孩,还有一个戴着棒球帽、没有脸的男人。
秦岚研究着它:“为什么没有脸?”“她不信任脸,”江哲说,“但她信任存在。
”秦岚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低声说:“我从来不知道。”“没人告诉你,
”江哲温和地说,“你太忙于建立一种,能将悲伤拒之门外的生活。
”秦岚的声音颤抖了:“但它还是进来了。”江哲点点头:“它总是会。”午餐时,
秦诺留下来打扫安静房间。她叠好豆袋沙发的套子,重新排列了白板上的磁铁,
并轻轻地把一支弯曲的蜡笔弄直。秦岚在门口看着。“你不必做这个。
”秦诺没有抬头:“我想做。”秦岚走了进去:“我能帮忙吗?”秦诺耸了耸肩。
她们在沉默中一起整理了房间。然后秦诺轻声但清晰地说:“爸爸过去常说,
你无法控制风暴何时来临,但你可以选择在哪里建造你的避难所。”秦岚僵住了,
然后慢慢地坐在女儿旁边:“这是你的避难所吗?”秦诺环顾四周:“这是第一个,
我不需要坚强的地方。”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江哲独自站在714房间,调整灯光,
更换用旧的马克笔,在画架旁放上新纸。江念出现在门口。“她今天叫你江叔叔了。”她说。
江哲笑了:“是讽刺的吗?”江念摇摇头:“听起来像是信任。
”然后她递给他一颗折好的纸星星。他打开它。
里面是江念圆圆的笔迹:“谢谢你建造了一个,我的声音不是唯一重要的房间。
”江哲艰难地咽了一下:“我没有建造它,”他说,“是她们。我只是确保没人把它拆掉。
”雨是在大楼灯光渐暗时开始下的,在玻璃墙上划出道道银色的河流。江哲站在保洁间旁,
静静地折叠着一张破旧的建筑蓝图,那是几周前他在一个满是灰尘的柜子里找到的。
他那双因多年劳作而依旧粗糙的手,抚摸着那些线条,仿佛它们是记忆。
江念盘腿坐在一只倒置的木箱上看着他:“你总是看着那些,好像它们是活的。
”江哲淡淡地笑了:“每栋建筑都有一个故事。你可以从支撑它的线条中看到。
”“你觉得人也像那样吗?”江念问。江哲停顿了一下:“是的。只是人的蓝图更凌乱。
有些线条断了,有些墙太薄。但如果有人相信它们值得修复,它们仍然会屹立不倒。
”江念歪了歪头:“那你为什么不让任何人修复你的呢?”江哲的手停住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第二天早上,林溪把秦岚叫进她的办公室。她的声音带着那种罕见的严肃,
那种能穿透所有总裁虚张声势的语调。“您需要知道这个男人是谁。”林溪说着,
把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放到玻璃桌上。秦岚皱起了眉:“江哲。”“是的。或者我该说,
江哲博士,言语治疗师,儿童康复专家。他曾是天才,是国内最顶尖的之一。
”秦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曾是?”林溪犹豫了一下:“三年前,他失去了一个病人。
一个患有罕见病的小女孩。他一直在帮她找回声音,但她……”林溪的声音柔和下来,
“她没能挺过去。后来有一场官司,不白之冤。他被证明无罪,但他完全离开了那个领域。
”秦岚盯着文件夹。
这与那个拖着她走廊、与她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却不要求他们改变的安静男人完全不符。
“他不仅仅是个保洁员。”“不,”林溪说,“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他比您雇的任何人都更擅长这件事。”那天晚些时候,
秦岚发现江哲正在修理一个秦诺遗弃在楼梯上的破玩具——一只少了一边翅膀的发条鸟。
他弓着腰,工具摊在一块旧抹布上。“你曾是个治疗师。”她说。江哲没有抬头。
“你为什么在这里?”他拧紧一颗螺丝:“因为在这里,没人指望我拯救任何人。
”秦岚双臂交叉:“我的女儿们不是要修复的项目。”江哲终于抬起头看着她,
平静但坚定:“我不修复孩子。我倾听。这有区别。”“如果倾听不够呢?”她追问。
江哲把玩具鸟放在地上,轻轻地给它上发条。它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翅膀不均匀地扑动着,
但毕竟在移动。“那我就捧着那些碎片,”他说,“直到她们记起,自己本就注定要飞翔。
”秦岚的呼吸一滞。她不知道是因为这些话,
还是因为他眼中的神情——那种深知失败却仍选择相信的眼神。那天晚上,
秦诺带着沾满颜料的手指和一脸怒容冲进714房间。“我弄坏了东西。”她宣布。
秦默从她的速写本上抬起头:“什么?”“我的手表。妈妈很生气。
她说我需要照顾好重要的东西。但她甚至都没看见我。”江念的目光柔和下来。
她拿起一支画笔,开始在一张白纸上涂抹颜色:“你知道我爸怎么说吗?会坏掉的东西,
证明它们曾被足够地爱过、使用过。”秦诺皱起了眉:“那太蠢了。
”江哲的声音很温和:“或者,也许那是真的。也许你弄坏东西,
是因为你想看看有没有人足够在乎去修复它们。”秦诺盯着他。
她的嘴唇颤抖了:“从来没有人。”江哲蹲下来:“我不是在这里吗?”一瞬间,
秦诺的倔强动摇了。她把坏掉的手表放到他手心:“你能修好吗?
小说《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 治愈女总裁家那两个破碎的小千金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