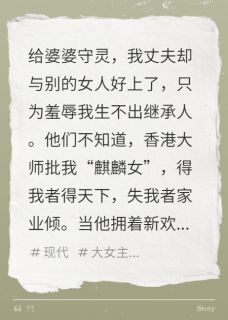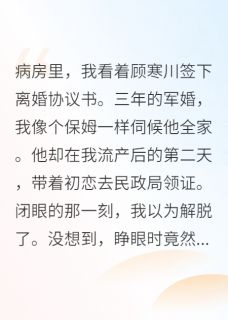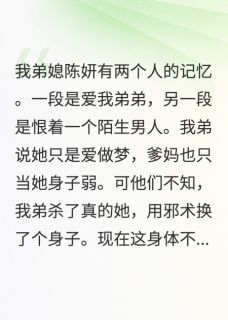《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小说简介
《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这篇由听飘秋写的小说,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一环扣一环。给人有种一口气看到底的感觉。主角是沈倦苏晚,《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简介:画笔饱蘸颜料,落下的不再是梧桐虬结的枝干,而是玉兰亭亭的倩影。笔尖划过画布的声音沙沙作响,轻柔得像在与一段旧时光作最后的……
《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 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第3章 免费试读
她举起蘸满颜料的画笔,朝他晃动,几滴金黄溅在雪白的画布上,晕开小小的、刺目的太阳。
“喂,你看这个色,像不像银杏道落满一地的叶子?等下个月铺了厚厚一层,我们来写生好不好?”
那时他正低头,专注地替她削着炭笔,细碎的木屑无声飘落,栖在她乌黑的发间,宛若一场温柔的碎雪。
“再说吧,”
他语气敷衍,却在无人处,用红笔在日历的十一月中旬重重画了一个圈——那是银杏叶最盛大、最悲壮的时节,是他们未曾赴约的秋日祭奠。
画室的门轴发出喑哑的**,风裹挟着迟桂浓稠的甜香涌入。抱着画框的学弟笑着招呼。
“沈倦学长,听社长说,你要退社了?”
沈倦猛地回神,像被窥见了隐秘的伤口,迅速将那罐冰凉的颜料塞进抽屉最深的角落。
“嗯。”
他应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空气中悬浮的尘埃,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掠过墙角那幅被尘封的画——荒芜的雪原上,那棵孤绝的梧桐树下,不知何时多了一株瘦小的、却奋力伸展枝桠的玉兰。
那是他后来,在无数个无眠的深夜,一笔一笔偷偷添上去的。
那时他固执地相信,只要再添上一点生机,画布上冻结的寒冬终将消融。
暮色如同浸了水的墨,缓缓漫过图书馆哥特式的尖顶。
沈倦独自穿行在归途,超市冰柜里整齐排列的橘子汽水,像一排排冰冷的琥珀,瞬间刺穿记忆的薄膜——苏晚总爱把冰镇的汽水瓶猝不及防地贴上他的后颈,看他惊跳起来,她便笑得前仰后合,眉眼弯成新月。
“沈倦!你的反应像只炸毛的兔子!”
她舔着唇角晶莹的汽水泡沫,眼里的光芒比玻璃瓶折射的光线还要璀璨,
“下次,我换冰可乐试试?”
鬼使神差地,他伸手拿了一瓶橘子汽水。扫码付款时,视线被收银台旁一串小巧的银杏叶挂坠攫住——那款式,与学长书包上曾别着的胸针,如出一辙。
指尖在空中悬停片刻,最终还是无声地收回。去年她的生日,他曾在这里买下同款挂坠,她欣喜地挂在钥匙扣上,称它为“专属护身符”。
后来某次歇斯底里的争吵,钥匙扣被她狠狠摔在地上,挂坠应声碎裂成两半。
他蹲在地上,徒劳地试图拼凑,裂痕却如同命运的分野,清晰而冰冷,再也无法复原。
宿舍楼下,公告栏的海报已换了新颜。文学社招新的信息被彻底覆盖,只余下“苏晚”名字的一角,倔强地从新海报边缘探出,像一只被强行掩埋的、折翼的蝴蝶。
沈倦仰起头,望向三楼那扇熟悉的窗。曾几何时,那里亮着他们共有的、暖黄色的灯光。
苏晚伏案疾书,他则在一旁,用铅笔在素描本上细细勾勒她柔和的侧影,笔尖摩擦纸页的沙沙声,曾是比晚风更温柔的夜曲。
手机的震动在寂静中格外突兀。母亲发来照片:庭院里,老梧桐的落叶铺了厚厚一层金黄的地毯,母亲蹲在树下,认真地捡拾着,配文说等他归来,一起将它们封存为时光的标本。
沈倦的指尖划过冰冷的屏幕,苏晚的身影蓦然浮现——她曾那样孩子气地将耳朵紧紧贴在梧桐树粗糙的树皮上,闭着眼,神情专注。
“沈倦!快来听!”
她兴奋地朝他招手,声音雀跃如林间小鸟,
“它在呼吸!它在说……欢迎我们回家呢。”
那一刻,空气里弥漫的,是银杏的微苦和阳光烘烤落叶的暖香,是再也回不去的秋日。
国庆前夕,樱花道已无樱花,只剩遒劲的枝干伸向灰白的天空。
苏晚的室友抱着一摞书迎面走来,看见他时微微一怔,随即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
“苏晚让我转交的……她说,这是最后一样了。”
信封轻若无物,里面只有一片被精心压平的玉兰花瓣,边缘已泛起陈旧的黄晕,像一页被遗忘在旧书里、褪了色的书签。
沈倦捏着这枚脆弱的花瓣,指尖能感受到它细微的叶脉纹路。
去年春天,苏晚也曾将带着晨露的玉兰花瓣夹进他的专业课本,笑着说这样翻开书就能闻到整个春天的气息。
“等明年玉兰再开,我们一起做书签好不好?”
她的声音落在书页间,与花瓣的清香一同,成了时光里最柔软的注脚。
然而今年的玉兰花开花谢,无人再提书签......
国庆归家,老梧桐的叶子几乎落尽,嶙峋的枝桠刺向高远的秋空,构成一幅苍劲而寂寥的素描。
母亲端出刚烤好的黄油饼干,香气四溢,她笑着说。
“苏晚去年说这个最好吃,我特意多烤了些。
那孩子……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母亲的目光不自觉地飘向门口,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
“你们不是说好,要在树下拍个照吗?”
沈倦拿起一块饼干,机械地咬下去,浓郁的甜腻在舌尖化开,却带出一丝难以言喻的苦涩。
“她……有事。”
他含糊地应着,视线却胶着在墙角那本厚厚的标本册上——里面珍藏着去年他与苏晚共同拾捡的梧桐叶,每一片叶子的背面,都工整地写着日期,像一串被时光琥珀封存的、无声的密码。
入夜,秋风渐起,吹动窗外梧桐稀疏的残叶,发出沙沙的低语,如泣如诉。
沈倦坐在书桌前,就着台灯昏黄的光,再次翻开那本承载着过往的日记。
中间某一页,用稚拙却充满生机的线条画着一个篮球场:一个穿着火红球衣的身影高高跃起投篮,旁边站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高举着一瓶可乐,笑容灿烂得仿佛要溢出纸面。
底下是一行娟秀的小字:“今天他输了比赛,却笑得像个傻瓜。
因为我请他吃了烧烤,他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陪着一起难过。”指尖轻轻抚过那行字,炭火的暖意、烤玉米的焦香、苏晚被炭火映得发亮的侧脸……记忆汹涌而至。
他曾天真地以为,那样的夜晚,会是他们漫长生命里无数个相似的片段。
日记的最后几页是令人窒息的空白,直到最后一页——没有日期,没有文字。
只有一片用铅笔细细勾勒的、飘零的银杏叶,孤单地悬在纸页中央,叶尖向下,像一滴凝固在时光尽头、永不坠落的泪。沈倦长久地凝视着它,胸腔里翻涌着迟来的钝痛。他终于明白,所有的离别,在故事开篇的第一笔,或许就已埋下了伏笔。
返校的行李箱里,沈倦悄悄放入了一片新摘的梧桐叶。叶面还带着清晨露水的凉意,脉络清晰如掌纹。
他想像她从前那样,做最后一次无声的告别,将这片“季节的明信片”悄悄夹进她某本不常用的课本里,如同归还一段失落的时光。
然而,命运并未给他这个机会。
回校首日,图书馆三楼的回廊。熟悉的桂花香已淡去,只剩下清冷的空气。
沈倦猝不及防地撞见了苏晚和学长。他们并肩立于巨大的落地窗前,学长指着窗外层林尽染的银杏道,低声说着什么。
苏晚侧耳倾听,唇角弯起一抹极淡的笑意,发尾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曳,像一只终于寻获栖息之所、安然振翅的蝶。
沈倦下意识地后退一步,隐入书架投下的阴影。
他手中的梧桐叶却像有了自己的意志,挣脱了指尖的束缚,翩然飘落在地,发出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声响。
苏晚的目光被惊动,扫了过来。她的视线在那片新鲜的梧桐叶上停留了极其短暂的一瞬——短过掠过一粒尘埃。
随即,那目光便平静地移开,投向窗外更辽远的秋色,再无波澜。
学长却已弯腰,拾起了那片叶子。他走向沈倦,脸上带着温和而疏离的笑容,将叶子递还。
“同学,你的东西掉了。”
沈倦接过那片叶子,指尖触及叶脉冰凉的触感。
苏晚清脆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沈倦你听!每片叶子碎掉的声音都不一样呢!”
那么,这片跨越城市、带着故园气息的叶子,它无声的坠落,该怎样诉说它无法言说的心事?
他沉默地攥紧叶子,转身走向楼梯口。身后,传来学长温和的提议。
“那片叶子形状很特别,我们也去捡几片做标本吧?”
苏晚的声音轻飘飘地传来,像一片终于决定落地的银杏叶。
“好啊。”
脚步声混合着低语,渐渐消失在回廊深处,浓郁的桂花香依旧固执地弥漫在空气里。
沈倦用力呼吸,却只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肺腑深处弥漫开来,冻结了四肢百骸。
十二月初的黄昏,雪籽开始试探性地敲打画室的玻璃窗,发出细碎而清冷的声响。
沈倦最后一次整理自己的物品,准备彻底告别这个装满回忆的空间。
画板上,依旧贴着苏晚画的那棵歪歪扭扭却生机勃勃的梧桐树,旁边那句“沈倦的树,要长到天上去!”的字迹,在经年的日晒下已有些褪色发白,像一句被风干、被遗忘在时光角落的古老誓言。
他伸手,准备揭下这最后的印记。指尖触碰到画纸边缘时,却意外地感觉到一丝微弱的粘滞。
他小心翼翼地掀起一角——画纸的背面,竟然还粘着一张小小的、同样褪色的便利贴!
熟悉的娟秀字迹,带着一种他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近乎祈求的温柔,静静呈现:
“沈倦的树,要一直往上长,别停下哦。”
字迹的末尾,被一滴早已干涸、晕染开来的泪痕模糊了形状,如同一朵在绝望中悄然绽放的、透明而哀伤的花。
沈倦的心猛地一沉,仿佛被无形的重锤击中。
他屏住呼吸,用指尖最轻柔的力道,小心翼翼地将这张承载着最后叮咛与泪水的纸片剥离下来,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稀世珍宝,郑重地夹进那本写满过往的日记本里。
窗外的天色彻底暗沉下来,雪籽敲打玻璃的声音愈发密集。
他蓦然想起去年深冬,苏晚也是这样蜷在画室的暖气旁,画着那幅覆盖着厚厚白雪的梧桐。
画布上,雪温柔地包裹着虬结的枝干。
“沈倦你看,”
她指着画中的树,眼底有细碎的光在跳动,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笃信,
“雪会保护它的,这样它就不会冷了。”
直到此刻,站在彻底失去她的寒冷里,沈倦才痛彻心扉地领悟:原来这世间有些彻骨的寒意,是连最纯净的雪,也无法温暖的。
办完退社手续的那天下午,篮球场上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比赛。
当终场哨声响起,最后一秒的压哨球应声入网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浪几乎掀翻屋顶,热烈的程度与去年如出一辙。
沈倦独自坐在看台最高、最偏僻的角落,喧嚣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
眼前晃动的人影与欢呼,瞬间与记忆重叠——那个抱着冰镇可乐、不管不顾冲进球场的娇小身影,汽水洒在他汗湿的红色球衣上,冰凉而甜腻的触感似乎还停留在皮肤上。
那时的风里,鼓胀着青春无畏的喧嚣和心跳失序的轰鸣。
比赛散场,人群如潮水般退去。
沈倦逆着人流,走向宿舍。路过公告栏时,那张曾印着苏晚名字的文学社海报,已被崭新的、印着烫金大字的新年晚会通知彻底覆盖。那抹清秀的字迹,如同从未存在过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驻足,在暮色四合中凝视着那片刺目的红,直到寒意爬上肩头,才默默转身。
路过那排沉默的玉兰树时,脚步再次凝滞。苏晚和学长正在树下堆雪人。
学长卖力地滚着雪球,苏晚则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将一朵廉价的塑料玉兰花插在雪人光秃秃的头顶。
她拍着手,看着自己的“杰作”,笑得眉眼弯弯,呵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氤氲开。
那根系在腕间的红绳,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红得刺目,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昭示着过往的伤痕。
沈倦忽然想起,她曾那样怕冷,冬天总要把自己裹成一只笨拙的熊,还要把冰凉的手塞进他的口袋取暖。
可此刻,她站在凛冽的寒风里,脸颊冻得微红,笑容却明媚得仿佛能融化冰雪。
他没有停留,径直拐进旁边一条僻静的小路。
校门外的老梧桐,枝桠上已覆了一层薄薄的初雪,像披上了一件素缟的外衣。沈倦伸出手,接住一片悠然飘落的雪花。
那冰冷的六角晶体在掌心迅速融化,只留下一小滩微凉的水迹,像一滴无声滑落的泪。
手机在口袋深处震动起来。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突兀地躺在屏幕上:
“我要转学了,勿念。”
没有任何称谓,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
沈倦盯着那短短七个字,屏幕的光映亮了他毫无表情的脸,直到光线彻底暗下去,屏幕变成一片漆黑的镜子,映出他模糊而疲惫的轮廓。
记忆的闸门轰然开启——手机第一次收到她的消息,那个遥远的春日午后。
“沈倦,我是苏晚,就是在梧桐树下……偷看你很久的那个女生。”
那时的消息提示音,曾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荡起圈圈名为期待的涟漪。
新年晚会那晚,校园里张灯结彩,人声鼎沸,歌声与笑闹声隐隐传来,像一场盛大而遥远的背景音。沈倦没有去。
他独自坐在图书馆三楼空旷的回廊里,窗外,雪落无声,又时停时续。
桂花香早已散尽,唯有刺骨的寒意,穿过窗棂的缝隙,悄然落在摊开的日记本上。
在最后一页,那片孤独飘零的银杏叶旁,他提起笔,蘸着窗外清冷的月光,写下了一行新的注脚:
“雪原上的树,其实……等过春天。”
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远处的晚会歌声达到**,热烈得如同最后的狂欢。
沈倦合上日记本,起身离开。路过那排玉兰树时,那个顶着塑料玉兰花的雪人依然孤零零地伫立着。
廉价的花瓣在雪地的反射下,闪烁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微弱的荧光,像一只被冻僵在寒冬、再也无法飞走的蝴蝶。
细雪又开始无声飘洒,落在沈倦的头发、肩头,带来冰凉的触感。
他仰起脸,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几片雪花落在睫毛上,瞬间融化,像一场来自天空的、温柔而冰冷的告别。
行至校门口,一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正缓缓启动。
车窗摇下,露出苏晚清瘦的侧脸轮廓。她微微低着头,正对身边的学长说着什么,唇角似乎带着一丝浅淡的笑意。
那根刺目的红绳在她纤细的手腕上只闪现了一瞬,便被迅速升起的车窗彻底隔绝。
沈倦定在原地,像一尊凝固的雕像,看着那辆黄色的出租车碾过薄薄的积雪,汇入昏黄路灯下的车流,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道路尽头,如同被呼啸的风卷走的一粒尘埃。
他忽然从口袋里摸出那片早已干枯、却被他一直珍藏的梧桐叶。
叶片脆弱,叶脉却依然清晰深刻,如同镌刻在时光深处的古老纹路。
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这片来自故园老树的叶子,轻轻放在冰冷的、未被踩踏过的雪地上。
然后,挺直脊背,转身,朝着来时的方向,一步一步,踏雪而归。
身后,新落的雪片温柔地覆盖了他留下的脚印,很快便抹平了所有痕迹,仿佛从未有人在此驻足、凝望、告别。
回到宿舍,书桌上静静躺着一个来自远方的包裹。拆开,是母亲寄来的一本崭新的、厚实的标本册。素雅的扉页上,是母亲熟悉的字迹:
“新的叶子,总要和新的人,一起捡拾新的阳光。”
沈倦捏着那本散发着淡淡纸墨香的册子,走到窗前。
窗外,细雪无声,正温柔地落在老梧桐光秃的枝桠上,渐渐积起一层更厚的白。
他凝望着那棵沉默的树,眼前浮现苏晚曾那样虔诚地将耳朵贴在粗糙树皮上的模样,她说她能听见树的呼吸。
或许,树真的在呼吸。
它呼吸着每一季的风霜雨雪,呼吸着每一个曾在它荫蔽下驻足、欢笑、哭泣、最终离去的人。
它沉默地见证,无声地铭记,然后,在下一个春天,再次沉默地吐出新绿。
开春,泥土解冻,空气里弥漫着万物萌动的气息。
沈倦带着铁锹和水壶,再次来到老梧桐树下。他选了一处向阳的角落,挖开湿润松软的泥土,小心翼翼地将一株玉兰幼苗的根系埋入。
他不知道它能否成活,能否开出洁白的花朵,就像他不知道未来的旅途上,会遇到怎样的风景,怎样的人。
但他想,当这株玉兰终于绽放的那一天,风里或许会萦绕着一种全新的、清冽的芬芳,像一个等待被重新书写的故事开篇。
那天的阳光格外慷慨,暖融融地洒在刚翻新的、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土壤上,温柔得像一句来自大地的无声承诺。
沈倦蹲在树旁,指尖深深插入湿润微凉的泥土中。就在这一刻,苏晚曾说过的话,带着阳光的温度,清晰地回响在耳边:
“每粒沉睡的种子心里,都藏着一个不肯认输的春天。”
或许,是的。
或许所有的离别,并非故事的终点。
就像老梧桐年复一年地落叶,又会在春风里重披新绿;就像玉兰凋零了花朵,却孕育着来年更盛大的绽放。
就像他们,终究要在这各自延伸、不再交汇的时光长河里,独自穿越风雨,慢慢学会成长,长成自己生命里,那棵沉默或繁茂的树。
小说《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 我睁眼去寻,却只能在梦中见你。第3章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