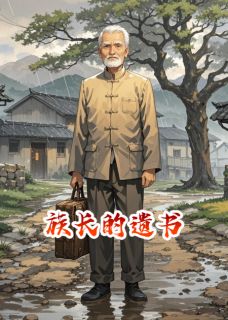《族长的遗书》小说简介
叶照金牙彪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年轻剑客,他在叶海洋的小说《族长的遗书》中,踏上了一段以复仇为目标的惊险之旅。被背叛和家族血仇所驱使,叶照金牙彪不断面对强大的敌人和迷失的自我。这部[标签:类型]小说带有浓厚的武侠风格,情节扣人心弦,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和力量的较量,像被踩住尾巴的野猫,声音里裹着浓浓的恐惧,惊得田埂里的青蛙都住了声。正在值夜的叶老三握紧**,枪身是他爹传下来的老套筒,……必将让读者沉浸其中,回味无穷。
《族长的遗书》 族长的遗书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1第一章:归乡第一章:归乡阴沉的天空仿佛被厚重的铅云压得喘不过气,
细密的雨丝如银针般斜斜洒落,将潮海市监狱的灰色高墙浸润得愈发黯淡。斑驳的墙面上,
岁月留下的裂痕里蓄满了雨水,在这压抑的氛围中,锈蚀的铁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缓缓向两侧敞开。63岁的叶照迈着略显蹒跚的步伐走出铁门,
身上那件洗得发白、满是补丁的中山装早已被雨水打湿,紧贴在他形容枯槁的身躯上。
二十年的牢狱时光,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如霜,
唯有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透着历经沧桑后的坚韧与冷峻。他提着破旧的行李,
那行李袋边角磨损严重,露出里面零星的几件旧衣物,仿佛在诉说着这些年的艰辛。
监狱外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陌生的霓虹广告牌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街边店铺的电子屏不断变换着色彩鲜艳的画面,一切都显得那么喧嚣而陌生。
叶照站在监狱门口,目光略显迷茫地扫视着四周,他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已无至亲之人,
本就不抱有人来接他的期望。不远处,几个路人停下脚步,对着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眼神中或带着好奇,或带着鄙夷。他没有在意,只是微微眯起眼睛,任由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仿佛要借此冲刷掉身上的晦气。“这人刚从牢里出来吧,看着就不像好人。”“可不是嘛,
也不知道犯了啥罪,这么老了才放出来。”路人的议论声如针尖般刺入耳中,
叶照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行李袋的提手。二十年的牢狱生活,他早已习惯了被人误解,
可此刻,这些话语还是让他心中泛起一阵刺痛。他深吸一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转过街角,
踏上了一条泥泞的乡路。雨水混着泥土,在脚下形成了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水洼,每走一步,
都能听到鞋底与泥浆的摩擦声。这条曾经熟悉的路,此刻却显得如此漫长而陌生。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二十年前的那个雨夜,也是这样的雨丝,也是这样泥泞的小路。
那时的他,年轻气盛,为了保护村里的利益,与邻村发生冲突,
最终因过失致人死亡锒铛入狱。临行前,村民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惋惜与不舍,而如今,
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不知道,村民们是否还能接纳这个“罪人”。
足足走了大半天,就在这时,前方的雨幕中,一道人影渐渐清晰起来。叶照定睛一看,
竟是叶家村的七叔公。老人已是八十高龄,白发苍苍,背佝偻得像一张弯弓,
却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长衫,拄着一根雕刻着精美花纹的木质拐杖,
在雨中立得笔直。在七叔公身后,叶家村的百十口男女老少整齐地排列着,
沉默地伫立在冷雨中。孩童们懵懂无知,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望着叶照,
有的小手紧紧攥着大人的衣角,有的在雨中瑟瑟发抖;老人们浑浊的眼中满是泪水,
用衣袖不停地擦拭着,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青壮年们神情严肃而坚定,
眼神中既有对叶照归来的欢迎,又夹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复杂神色。
整个场面在雨雾的笼罩下,宛如一幅凝重而震撼的油画。叶照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二十年了,自他被带走的那一天起,
他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场景。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人群,
试图从那些变化巨大的面容中找寻往昔的记忆。“照娃啊,”七叔公颤巍巍地向前迈出几步,
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艰难,却又无比坚定。“这些年,苦了你了。
”老人的声音在雨中微微颤抖,带着浓浓的心疼与愧疚。叶照喉咙发紧,想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太多太多,他与七叔公之间,
仿佛隔了一道无形的墙。七叔公走到叶照面前,浑浊的老眼中满是欣慰与感慨,颤抖着双手,
从怀中取出一枚旧族印。那族印历经岁月的摩挲,表面早已发亮,
刻着“叶氏宗族”四个古朴的大字,边缘还雕刻着精美的云纹,是叶家村族长权威的象征。
“村里不能没有主心骨,这族印,还是得交给你。”七叔公将族印郑重地放在叶照掌心。
“这些年,村里没了主心骨,日子过得艰难啊。邻村老是来抢咱们的水源,
年轻人也都人心惶惶,不知道该咋办。”叶照只觉得掌心一沉,
一股温热的感觉顺着指尖传遍全身。他冰冷坚硬的心第一次剧烈震颤,眼眶不禁湿润起来。
他紧紧握住族印,声音沙哑地说:“七叔公,我……我坐了二十年牢,
还有资格当这个族长吗?”“傻孩子。”七叔公伸手轻轻拍了拍叶照的肩膀。“当年的事,
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村子。这些年,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人群中,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忍不住抽泣起来:“照娃啊,你可算回来了,这些年,村里没了你,
就像没了魂儿似的。”“是啊,照叔,我们都等着你带领咱们重新把日子过好呢!
”几个年轻小伙也纷纷喊道。叶照的目光再次扫过人群中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心中五味杂陈。感动、愧疚、责任,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深吸一口气,
大声说道:“乡亲们,谢谢你们还愿意相信我。从今往后,我叶照一定不会再让大家受苦,
一定守护好咱们叶家村!”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个细微的动作引起了叶照的注意。
阿霞嫂正搀扶着她残疾的儿子,那孩子因幼时的一场意外,双腿无法正常行走,
只能依靠母亲的搀扶才能勉强站立。阿霞嫂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是因为雨中的寒冷,
还是内心的紧张。她丈夫叶炎在二十年前与邻村的一场群架中丧生,留下这对可怜的母子俩。
叶照心中一紧,快步走到阿霞嫂面前,蹲下身,看着她儿子的眼睛,轻声说:“孩子,别怕。
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叔说。”然后转头对阿霞嫂说:“嫂子,这些年,辛苦你了。
叶炎兄弟的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以后,我会照顾好你们娘俩的。”阿霞嫂泪水夺眶而出,
哽咽着说:“照娃,我知道你是好人。当年要不是你,村里的损失会更大。这些年,
我带着孩子,虽然日子苦了点,但也熬过来了。现在你回来了,咱们村就有希望了。
”而年轻一辈的叶明辉,眼神闪烁不定,嘴角不经意间微微一撇,流露出一丝不屑与不服。
他的父亲叶贵,为了救叶照用身子为叶照挡了一枪,倒在叶照怀里离世了。
叶明辉心中一直认为父亲的死是叶照害的,他从小就将叶照恨之入骨。叶照站起身,
走到叶明辉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明辉,我知道你恨我。当年你父亲的事,
是我对不起你和你们一家。这些年,我在牢里,每天都在想这件事,
心里的愧疚一刻都没停过。但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一定会用余生来弥补。
”叶明辉冷哼一声,别过脸去,说:“弥补?我父亲的命没了,怎么弥补?”“明辉,
别这样。”七叔公拄着拐杖走过来。“照娃也是为了保护大家,你父亲的牺牲,
他比谁都难过。这些年,他在牢里受的苦,也算是一种惩罚了。现在他回来了,
咱们应该团结起来,把村子建设好,这才是你父亲希望看到的。”叶明辉沉默不语,
只是咬着嘴唇,眼中满是矛盾与挣扎。在众人的簇拥下,叶照朝着叶家村的方向走去。
雨依旧在下,却似乎不再那么冰冷。远处,叶家村的轮廓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袅袅炊烟从村落中升起,与雨雾交织在一起。叶照的心中,涌起一股回家的温暖,
同时也暗暗下定决心,无论未来会遇到多少困难,他都要守护好叶家村,
重拾曾经的荣耀与安宁。一路上,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向叶照诉说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谁家新添了孩子,谁家的老人去世了,邻村又有哪些刁难,桩桩件件,叶照都听得格外认真。
他知道,自己离开得太久,需要尽快熟悉这些变化,才能更好地带领大家。“照娃,你看,
那片果园,原本是咱们村的,可现在被邻村占了大半。”一位村民指着远处的一片果园说道。
叶照眉头紧皱,眼神中闪过一丝怒意:“他们凭什么占我们的地?
”“还不是因为咱们村没个能做主的人,他们就欺负咱们。”另一位村民气愤地说。
叶照握紧了拳头,说:“放心,这件事我会解决。咱们叶家村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
”回到村里,叶照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
老槐树依然屹立不倒,只是树干上又多了几道岁月的痕迹。树下的石磨,也早已布满了青苔。
“照娃,走,先回你家看看。”七叔公说,“这些年,我们一直派人打扫着,没让它荒废。
”叶照跟着七叔公来到自家门前,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虽然屋里的摆设都已陈旧,但却干净整洁。墙上还挂着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
笑容灿烂,眼神坚定。“这些年,变化太大了。”叶照感慨道。“是啊,不过现在你回来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七叔公说,“今晚,咱们全村人聚在一起,为你接风洗尘。”当晚,
村里的晒谷场上摆起了长桌,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家的好酒好菜。火光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庞,
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村庄。叶照坐在主位上,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心中充满了感动。
酒过三巡,叶照站起身,举起酒杯,说:“乡亲们,感谢大家还把我当自己人。从今天起,
我叶照就是咱们叶家村的族长,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让咱们村过上好日子。
邻村欺负咱们的事,我会解决;村里的发展,我也会想办法。我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支持我,
咱们一起把叶家村建设得更好!”“我们相信你,照娃!”村民们纷纷举杯响应。
叶明辉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着酒,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中,似乎有了一丝动摇。夜深了,
村民们渐渐散去。叶照站在自家院子里,望着满天繁星,思绪万千。二十年的牢狱生活,
让他失去了太多,但如今,他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他知道,前方的路充满挑战,
但他无所畏惧。为了叶家村,为了这些信任他的乡亲们,他愿意付出一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叶照开始着手处理村里的各种事务。
他先是组织村民们修缮了村里的水利设施,解决了灌溉问题;然后又与邻村进行谈判,
通过各种方式,夺回了被占的果园。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的年轻人也有了干劲,
大家齐心协力,为村子的发展努力奋斗。叶照也没有忘记阿霞嫂母子,他经常去看望他们,
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渐渐地,阿霞嫂的儿子脸上有了笑容,对叶照也亲近了许多。
而对于叶明辉,叶照始终没有放弃。他经常找叶明辉谈心,向他讲述当年的事情,
表达自己的愧疚。叶明辉并不理会,他只觉得叶照很虚伪。二十年的牢狱生涯,
让叶照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也让他更加懂得了责任与担当的意义。他知道,自己的人生,
从归乡的那一刻起,才真正开始。2第二章:怒焰燃坟破晓时分,
铅灰色的云层还压在叶家村的屋脊上。叶照裹紧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踩着沾满晨露的石板路出门。昨夜他在祠堂枯坐了整宿,油灯将熄未熄时,
他盯着族谱上被虫蛀出的窟窿,终于在泛黄的纸页间找到了老周头家宅基地的分册记录。
老周头家的茅草屋蜷缩在村西头,歪斜的房梁在晨风里发出吱呀的**。
叶照抬头打量摇摇欲坠的屋顶,檐角垂下的蛛丝混着霉斑,
在他眼底勾勒出二十年前的画面——那时他刚当上族长,带着全村人帮老周头盖起这新房。
"搭梯子!"叶照扯下外套,露出布满老茧的臂膀。晨光斜斜切过他脸上的沟壑,
几缕白发被风掀起,在额前晃成一片霜色。几个青壮年闻声跑来,
却见族长已经手脚并用爬上屋顶,碎瓦片在他掌心划出细长的血痕,
殷红的血珠顺着指缝滴落在褪色的灰瓦上。"照叔,我来换你!"年轻的阿强伸手要接瓦片。
叶照头也不回,粗粝的声音混着风声。"你们递材料,这房梁我得亲自校准。
"他记得老周头老伴瘫痪在床,记得这屋顶漏雨时浸湿的被褥,记得二十年前那场暴雨里,
他和老周头在泥水里抢收稻谷的模样。日头升到中天时,叶照简单包扎了伤口,
带着十几个村民直奔邻村边界。被侵占的田埂上,新插的界碑歪斜地杵在泥土里,
碑身刻着邻村"李"字的族徽。叶照站在自家稻田的残茬间,脚下是被践踏的稻根,
远处传来抽水机的轰鸣——本该灌溉叶家村农田的水渠,此刻正哗啦啦流向邻村的鱼塘。
"李长贵!"叶照的声音像块淬了冰的铁,在空旷的田野上炸开。邻村村长叼着烟踱过来,
身后跟着七八个壮硕的汉子。"叶照?"李长贵吐了口烟圈,"坐完牢还管闲事?
这地三年前就划给我们了。"叶照蹲下身,指尖摩挲着田埂上新鲜的车辙印。
"民国二十三年的地契,写得清清楚楚。"他突然攥起一把黑土,泥土从指缝簌簌落下。
"当年我爹和你爷爷,就是在这条田埂上歃血为盟。"话音未落,他猛地将泥土扬向天空,
碎土纷纷扬扬落在李长贵肩头。空气瞬间凝固。李长贵的脸涨得通红,
身后的汉子们蠢蠢欲动。叶照却纹丝不动,鹰隼般的目光扫过众人。"三天后,我带地契来。
要是还在这见到你们的人..."他顿了顿,露出半截染血的绷带。"这条田埂,
会记得叶家的血是什么颜色。"处理完田地纠纷,暮色已经漫过村头的老槐树。
叶照刚踏进祠堂,就听见村口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他转身疾步走去,
只见几个染着黄毛的混混正踢翻王婶的菜摊,青黄的菜叶混着泥水,在地上铺开一片狼藉。
"住手!"叶照的怒吼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为首的黄毛歪戴着鸭舌帽,
吐着烟圈上下打量他。"哪冒出来的老东西?"话未说完,叶照已经揪住他的衣领,
将人抵在斑驳的土墙上。混混腰间的匕首滑落,在石板路上撞出清脆的声响。"告诉金牙彪,
"叶照的拇指狠狠抵住黄毛的喉结。"叶家村的规矩,不是他能坏的。"黄毛涨红着脸挣扎,
喉间发出嗬嗬的气音。围观的村民越聚越多,阿霞嫂抱着儿子躲在人群里,
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二十年前,正是这样的场面,让她失去了丈夫。祭祖日的清晨,
乌云压得更低了。叶家村的男女老少身着素衣,沿着蜿蜒的山道走向祖坟。叶照走在最前方,
手中捧着族谱的匣子,
指腹无意识摩挲着匣子上的裂痕——那是昨夜发现族谱被人恶意损毁时,他失手摔的。
祖坟前的供桌上,鸡鸭鱼肉蒸腾着热气,檀香袅袅升起。叶照刚点燃三炷香,
突然听见人群中爆发出尖叫。他转身的瞬间,瞳孔猛地收缩——三座祖坟的封土被刨开,
青砖散落一地,破碎的墓碑斜插在泥地里,"叶氏族谱"的石碑上,
鲜红的油漆涂满了"老狗"二字。更刺眼的是那根竹竿,上面挂着的布条在风中猎猎作响,
暗红的字迹还在往下滴着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血水。孩童的哭声、老人的啜泣声此起彼伏,
叶明辉突然冲出人群,指着叶照嘶吼。"我说什么来着!你一回来就没好事!
二十年前害了我爹,现在又连累祖宗!"骚动的人群像被惊扰的蚁穴,议论声嗡嗡作响。
叶照感觉太阳穴突突直跳,二十年的牢狱生涯教会他隐忍,此刻却有团火在胸腔里炸开。
他盯着石碑上被刮花的族谱二字,想起昨夜祠堂里,七叔公用颤抖的手抚摸族谱残页时,
浑浊的泪水滴在他手背上的温度。"都住口!"叶照的吼声震得香案上的烛火摇晃。
他大步走到祖坟前,单膝跪在翻涌的泥土上,徒手挖开潮湿的坟土。指甲缝里渗出血珠,
混着祖先的骨殖,他却浑然不觉。当他捧起那把带着体温的泥土时,
祠堂里供奉的历代祖先牌位,似乎都在云层的阴影里发出无声的叹息。"叶家的骨头,
从来不是泥捏的!"叶照高举着泥土,发丝被狂风吹得凌乱。"金牙彪想要血债血偿?
"他突然将泥土重重摔在石碑上,暗红的泥点溅在"老狗"二字上。"我叶照的血,
早就和叶家的地融在一块了!"人群渐渐安静,只有风声呜咽。叶照转身扫视众人,
目光如刀:"七日内,全族青壮,修缮祖坟!从今日起,村口设岗,入夜宵禁!
"他的视线最后落在叶明辉身上,后者下意识后退半步,却撞上了阿霞嫂怀中的孩子。
那孩子突然放声大哭,哭声在寂静的坟场里格外刺耳。暮色四合时,叶照独自站在祠堂门口。
远处的山峦隐没在雨幕中,他摸出怀中的族谱残页,上面"叶"字的最后一笔已经残缺不全。
祠堂里,七叔公点燃的长明灯在风中摇曳,恍惚间,他又看见二十年前那个雨夜,
父亲也是这样站在祠堂前,望着邻村方向的火把,将族长的族印郑重交到他手中。
雨终于落下来了,叶照仰头望着天空,任由雨水冲刷脸上的泥污。
金牙彪的挑衅、叶明辉的怨恨、村民们摇摆的目光,此刻都化作掌心的泥土,
在雨水中渐渐沉淀。他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的伤口——这场仗,才刚刚开始。
3第三章:雨夜祠堂午夜的雨丝裹着腥甜的铁锈味,顺着叶家村祠堂的青瓦缝隙渗进来。
神龛前的青砖地已经洇开巴掌大的深色水渍,像块不断晕染的墨团,
正一点点吞噬着供桌上褪色的红绸。檐角的铁马在风雨里发出喑哑的叮当声,
混着远处田埂里青蛙的聒噪,倒像是谁在暗处磨牙吮血。叶照蜷缩在供桌旁,
煤油灯芯爆出的灯花溅在他手背上,烫出个小米粒大的燎泡。他浑然不觉,
只是盯着黄纸上游走的墨痕发怔。粗糙的指节因为攥紧秃笔而泛白,指腹的老茧刮过纸面,
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二十年牢狱生涯刻下的印记,每个茧子都藏着磨破又愈合的血痂。
供桌底下堆着半筐发霉的稻谷,潮湿的霉味混着祖宗牌位前残留的香灰气息,
在鼻尖萦绕成一团混沌。他想起今早打扫祠堂时,从梁上扫下的麻雀尸骸,
干瘪的爪子还紧紧攥着根稻草,像个不肯瞑目的冤魂。“照哥!村口出事了!
”急促的砸门声裹着风雨撞进来,祠堂的木门发出痛苦的**。叶照猛然抬头,
笔尖在纸上划出道歪斜的墨痕,像条突然窜出的小蛇。
他迅速将写了一半的黄纸塞进祖宗牌位下方的暗格里,那地方是他亲手凿的,
砖缝里还嵌着年轻时磨镰刀的钢屑。起身时带翻的茶盏在地上碎成三瓣,
滚烫的茶水泼在布鞋上,烫得脚底板发麻,他却像踩着团棉花,半点知觉也无。祠堂外,
火把的红光将夜色撕成褴褛的布条。叶照拨开拥挤的人群,
木簪子别着的花白头发被风扯得乱晃。人群里混着浓重的汗味和尿骚气,
有个穿开裆裤的娃娃吓得直哆嗦,裤腿湿了大片,他娘慌忙用围裙去擦,
却蹭出片更深的污渍。村口老槐树上挂满了猩红的条幅,
“叶照狗命休矣”的血字在风里扭曲着,像一条条被剥了皮的蛇。有片血字被雨水泡得发胀,
顺着布纹滴下暗红的水珠,砸在树下的泥地里,洇出点点黑斑。斑驳的土墙上泼满了红漆,
顺着砖石缝隙蜿蜒而下,在墙根积成小小的红潭,几只蝼蛄挣扎着想爬出来,
却被黏住了翅膀。老周头的老伴瘫坐在地,怀里抱着被红漆浸透的棉被。
那棉被原本是雪白雪白的,绣着鸳鸯戏水的花样,现在却成了片污秽的红,
针脚里还卡着漆皮碎屑。老太太浑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棉被,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嚎。
“我的嫁妆啊……我攒了三年才织成的……”她的指甲深深抠进棉被里,带出些红漆渣子,
混着指缝里的泥垢,看着触目惊心。“是金牙彪的人。”叶文山压低声音凑过来,
这个四十岁的汉子额角还渗着血,血珠顺着眉骨往下滚,在颧骨上积成小小的血洼。
他手里攥着块沾血的破布,布纹里还缠着几根带泥的头发。“他们开着三辆摩托车,
边泼漆边喊让您自断双腿。”叶文山的声音发颤,不是怕,是恨。“带头的那个穿黑皮夹克,
后脖颈有道疤,我认得,是当年跟着金牙彪弟弟混的狗腿子。
”叶照的目光扫过围观村民惊恐的面孔。阿霞嫂正抱着昏迷的儿子泣不成声,
孩子额头上的伤口还在汩汩流血,血珠顺着脸颊滑进领口里,
把洗得发白的校服领子染出片深色。校服裤腿上沾着新鲜的泥印和机油,
膝盖处磨破了个大洞,露出里面渗血的伤口——显然是被摩托车恶意逼摔时蹭的。
旁边有个穿解放鞋的老汉想伸手去扶,却被阿霞嫂一把打开。“别碰我娃!
金牙彪的人不得好死啊!”夜风裹挟着血腥味掠过发梢,叶照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雨夜。
那时他刚满二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也是站在这祠堂前,
看着族里被邻村烧毁的谷仓。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噼里啪啦的燃烧声里混着妇女的哭嚎,
有袋没烧透的稻谷滚到脚边,焦糊的米粒粘在鞋面上,烫得他直跺脚。
只是那时的他年轻气盛,抄起墙角的镰刀就带着青壮冲了出去。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镰刀劈下去时带起的风声,比现在的雨声还要响。他记得金牙彪弟弟倒在地上的样子,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头被宰的猪,血从胸口涌出来,在泥地里积成小小的水洼,
把他的布鞋都泡透了。金牙彪当时跪在弟弟身边,指甲抠进泥地里,
发誓要让他叶照血债血偿。而现在,他摸了摸藏在腰间的族谱。那是本牛皮封面的旧书,
边角都磨得起了毛,里面夹着今早收到的匿名信。
泛黄的信纸上只有一行字:“金牙彪背后有人”,墨迹是蓝黑墨水,笔锋很劲,
像是用钢笔用力戳出来的。天未亮,祠堂的密室里就亮起了油灯。
潮湿的墙面上挂着用炭笔绘制的村落地形图,密密麻麻标着陷阱位置和巡逻路线。
图上的墨迹被水汽洇得发蓝,有些字迹已经模糊,
叶照用指尖在“老槐树下”四个字上反复摩挲,那里的炭粉沾了层薄灰。“你明天去县城。
”叶照将一个油纸包推过去,油纸被茶水浸得有些发潮,边角卷着毛边。
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最大面额是五十的,还有半截生锈的怀表,表盖已经掉了,
露出里面卡住的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找城西的瘸子阿四,他以前在金牙彪手下管账。
”叶照的声音很沉,像祠堂里的老钟。“记得,走小路,别带手机。顺着山涧走,
过了三道水闸再上公路,那里有辆拉煤的三轮车会等你。”叶文山接过东西时,
触到叶照掌心的老茧。那些茧子又厚又硬,像块块小石子,是二十年牢狱生涯留下的印记。
他在砖窑厂搬过砖,在采石场砸过石头,每个老茧里都嵌着洗不掉的泥灰。“照哥,
您真要拿自己当诱饵?”叶文山盯着桌上那封未写完的遗书草稿,泛黄的草纸上,
“残躯”二字的墨迹还没干,“躯”字的竖钩拉得很长,像把悬着的刀。叶照没回答,
只是往火盆里添了块木柴。松木在火里噼啪作响,爆出的火星溅在青砖地上,很快就灭了。
跳动的火苗映得他脸上的伤疤愈发狰狞,那道疤从眉骨一直延伸到下颌,
是当年在牢里跟人争窝头时被瓷碗划破的,缝了七针,现在摸上去还能感觉到凹凸的肉棱。
接下来的日子,叶家村像是座严阵以待的堡垒。村口竖起了带刺的竹篱笆,
竹子是刚从后山砍的,青绿色的竹皮上还挂着露珠,顶端削得尖尖的,闪着寒光。
老人们轮流坐在晒谷场织补渔网,那些浸过桐油的渔网又硬又韧,网眼里还缠着去年的稻壳,
他们的手指被渔线勒出深深的红痕,却没人吭声。叶照亲自带着青壮在村后山林埋设绊马索。
锋利的竹尖被削成倒刺,藏在厚厚的腐叶下,上面还盖着层伪装的枯枝。
他蹲在地上系绳结时,后腰的旧伤隐隐作痛,那是当年在采石场被石块砸的,
阴雨天就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站在山梁上俯瞰村落,
二十年前被大火烧毁的谷仓旧址如今种满了玉米,秸秆已经长到齐腰高,在风中沙沙作响,
像是无数双警惕的眼睛。远处的田埂上,有个穿红衣裳的娃娃在追蝴蝶,
那是阿霞嫂路边捡的小女儿,她哥哥还躺在家里发着高烧。金牙彪的攻势愈发凌厉。
三天后的深夜,三辆满载石料的卡车堵住了村办小厂的原料通道。卡车头喷着粗气,
前灯亮得晃眼,司机清一色蒙着黑口罩,露出的眼睛里满是戾气。叶照赶到时,
看到石料堆里埋着几只死老鼠,肚子鼓鼓的,显然是被毒死的,
腐臭的气息混着石料的粉尘弥漫在空气中,呛得人直咳嗽。“叶族长好手段。
”为首的司机扯下口罩,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牙床肉是红的,像是刚发炎。
他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带着血丝,“彪哥说了,明天日落前没见到您的双腿,
小厂就该换个新烟囱了。”深夜的祠堂再次亮起孤灯。神龛上的香炉里积着半截香灰,
是今早叶文山媳妇来插的,现在香已经燃尽了,只留下点火星。叶照展开那张泛黄的纸,
笔尖悬在“血脉”二字上方迟迟未落。墨汁在笔尖积成个小墨珠,眼看要滴下来,
他突然手腕一转,在旁边点了个小小的墨点。
二十年前那场大火的画面突然在眼前闪现:燃烧的谷仓里,木梁噼啪作响,
火星像萤火虫似的往上飞。他抱着族里的孩子往外冲时,横梁“轰隆”一声砸下来,
他下意识地把孩子护在身下,后背传来钻心的疼。醒来时就躺在警车的后座,铁栏杆冰凉,
硌得他后脑勺生疼。如今金牙彪步步紧逼,他知道,有些旧账该一并清算了。
就像祠堂里的老钟,该上弦了,不然就会一直停着,让人心里发慌。窗外突然传来瓦片轻响,
很轻,像只猫踩过。叶照的手顿了顿,将写完的遗书小心折成方块,棱角对齐,
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墨迹未干的字迹在昏暗中泛着诡异的光:“若我身死,勿寻仇。
族谱夹层有证,可保叶家太平。”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纸背都透出了墨痕。
他刚把遗书藏进牌位下的暗格,祠堂外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叶明辉举着火把站在月光里,
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年轻人脸上的表情在明暗交错间忽阴忽晴,
左边脸亮着,右边脸浸在阴影里。“明辉,你来做什么?”叶照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
祠堂里的香灰味似乎都被这声音冻住了。年轻人指了指远处,火把的光抖了抖,
映得他眼白上的血丝格外清楚。“村口的陷阱好像触发了,我来叫您。”转身时,
叶照瞥见他后腰别着的对讲机,黑色的机身,红色的信号灯在夜色中明明灭灭,
像只眨着的鬼眼。雨又下起来了,细密的雨帘把祠堂罩在里面,像个巨大的纱帐。
叶照望着祠堂外摇曳的火把,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同样潮湿的夜晚。
那时他以为自己能护佑全村平安,像棵老槐树似的,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却没想到会以囚徒的身份离开,走的时候,阿霞嫂还给他塞了个煮鸡蛋,用手帕包着,
温温热热的。如今,他摩挲着藏在袖中的族谱——那里夹着叶文山今早冒险带回的账本残页。
泛黄的纸上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最底下一行赫然写着金牙彪与某官员的资金往来,
日期是上个月初三,金额后面画着个小小的五角星,像是个标记。雷声在云层中轰鸣,
震得祠堂的窗户纸簌簌作响。叶照握紧了腰间的旧柴刀,刀柄被磨得发亮,
缠着的布条已经褪色。这把刀曾陪着他守护过叶家村,二十年前砍倒过金牙彪的弟弟,如今,
它将再次饮血。只是这一次,他要赌上的不只是自己的性命,还有整个叶家的未来。
就像牌位上的祖宗们,当年开垦这片荒地时,哪个不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祠堂外,
叶明辉的身影消失在雨幕中,对讲机的信号灯最后闪烁了一下,随即陷入黑暗。
雨丝落在叶照的脸上,冰凉冰凉的,他想起小时候娘给他讲的故事,说雨夜是老天爷在洗尘,
洗去不好的东西,留下干净的。他整了整衣襟,走出祠堂。火把的光在雨里散开,
像朵朵盛开的红梅。远处的老槐树下传来几声狗吠,很凶,像是发现了什么不速之客。
叶照的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在青石板的缝隙上,就像踩在命运的节点上,不偏不倚。
4第四章:子夜惊魂子夜的山风裹着腐叶与硝烟的气息,在叶家村上空盘旋。
祠堂的老梆子敲过三更时,木槌与梆子碰撞的余震还在梁上荡着,
村西头的狗突然集体狂吠起来。那不是寻常的预警,而是带着哭腔的嘶吼,
像被踩住尾巴的野猫,声音里裹着浓浓的恐惧,惊得田埂里的青蛙都住了声。
正在值夜的叶老三握紧**,枪身是他爹传下来的老套筒,铁管上锈得发绿,却依旧能打响。
他透过竹篱笆的缝隙望去,三道幽蓝的车灯划破黑暗,像毒蛇吐着信子蜿蜒而来。
车轮碾过碎石路的声响越来越近,混着劣质摩托车排气管的轰鸣,震得篱笆桩子都在发抖。
"有情况!"叶老三扯开嗓子大喊,声音劈得像被砂纸磨过。
他同时扣动了挂在篱笆上的铜铃,那铃铛是用旧马掌改的,边缘还带着钉孔,
此刻在他掌心剧烈摇晃,清脆的**瞬间撕裂了雨夜的寂静。紧接着,
此起彼伏的铜锣声从村子各个角落响起,东头晒谷场的铜锣最响,是聋子阿福敲的,
那汉子听不见声音,只知道拼命抡锤子,震得自己耳朵都红了。叶照从祠堂后屋翻身而起,
草席被他掀得滑到地上,露出底下潮湿的泥地。
藏在袖中的铁片硌得掌心生疼——那是他用二十年牢狱生涯磨出的利器,
是从采石场捡的弹簧钢片,被他在砖墙上磨了整整三年,边缘锋利得能刮开人的喉管,
背面还被他用指甲刻了个歪歪扭扭的"叶"字。金牙彪的手下"疯狗"一脚踹开虚掩的村门,
木门的合页"嘎吱"惨叫着断裂,带着木屑飞出去老远。
身后十几个混混举着汽油瓶和钢管鱼贯而入,汽油瓶里晃荡的液体在车灯下泛着油光,
有个瓶子的塞子没塞紧,顺着瓶身往下滴,在地上洇出深色的痕迹。
这个绰号源于他打架时总像野兽般撕咬对手的壮汉,此刻脸上蒙着块发黑的破布,
只露出一双猩红的眼睛。那眼睛里布满血丝,像是三天没合眼,瞳孔在车灯下缩成针尖,
死死盯着村里的方向。"给老子搜!抓几个崽子回去!"他的声音混着引擎的轰鸣,
粗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惊得路边草窠里的田鼠四散奔逃,有只慌不择路的撞在篱笆上,
发出细微的"咚"声。然而,他们没走出三步,脚下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
那声音在雨声里格外清晰,像咬碎了块冰。走在最前面的混混惨叫着跌进陷阱,
锋利的竹签瞬间刺穿他的小腿,竹尖从膝盖后面冒出来,带着点白森森的骨渣。
那混混疼得浑身抽搐,手里的钢管"哐当"掉在地上,在泥水里滚了几圈。紧接着,
挂在槐树上的渔网轰然落下,网绳是浸过桐油的,又硬又韧,将另外三人兜头罩住。
他们像被罩住的野猪,在网里拼命挣扎,却被渔线勒得更紧,
有个穿花衬衫的混混想扯掉脸上的网,手指刚碰到渔线就被割出了血,血珠滴在网眼里,
像缀了串红珠子。埋伏在暗处的村民们举着铁锹、锄头冲了出来,喊杀声响彻夜空。
叶老四举着把劈柴刀,刀背还沾着早上剁猪草的残渣;阿霞嫂新上门的男人扛着根顶门杠,
木头被他攥得发白,他今早刚从县城打工回来,
还没来得及换身干净衣裳;连七十岁的七叔公都拄着铁头拐杖冲了上来,
拐杖在地上捣得咚咚响,像在敲战鼓。混战中,"疯狗"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那水混着泥,
在他脸上冲出几道黑道子。他狞笑一声,露出两排黄牙:"就这点把戏?
"声音里的不屑像冰碴子,扎得人耳朵疼。他从腰间抽出一把西瓜刀,刀身是新磨的,
寒光在雨幕中一闪而过,映出他扭曲的脸。正当他要朝一个躲在树后的孩童劈去时,
那孩子吓得闭紧眼睛,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红薯干。一道黑影突然从屋顶跃下,
瓦片被踩得"哗啦"作响,碎渣子像雨点般落下。叶照的布鞋重重踩在他持刀的手腕上,
"咔嚓"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像踩断了根枯树枝。"老......老家伙!
"疯狗疼得冷汗直冒,豆大的汗珠混着雨水往下滚,砸在胸前的黑巾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叶照的袖中突然滑出一道银光。锋利的铁片精准地划开他的脸颊,
从眼角一直到嘴角,血珠顺着刀锋滴落,在地上砸出一朵朵红梅,
很快又被雨水冲成淡淡的红雾。叶照的动作快如闪电,左手卡住他的脖子,
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几乎要嵌进对方的肉里。右手的铁片抵住他的喉结,
冰凉的触感让疯狗浑身发抖。"当年我在牢里,用这玩意儿捅死过三个欺负新人的杂碎。
"叶照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却让疯狗的瞳孔骤然收缩。
混混们被这血腥的一幕惊呆了。有个举着汽油瓶的手一哆嗦,瓶子掉在地上,滚出老远,
幸好没碎。叶照的眼神冷得像淬了毒的匕首,扫视着周围瑟瑟发抖的众人,目光扫过谁,
谁就不由自主地往后缩。"告诉金牙彪,动叶家村一根草,老子让他断子绝孙!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炸雷般在每个人耳边响起。说罢,他狠狠一推,
"疯狗"踉跄着摔在泥地里,半边脸血肉模糊,血水混着泥水在他身下积成个小水洼。
他想爬起来,刚撑起身又"扑通"倒下,断了的手腕以诡异的角度歪着,像根折了的树枝。
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当金牙彪的手下连滚带爬地逃窜时,
有个跑慢了的被叶文山一锄头砸在腿弯,抱着膝盖嗷嗷叫;还有个慌不择路撞进了猪圈,
被老母猪追得满院子跑。叶家村的村民们举着火把站在村口,火把的光在他们脸上跳着,
映出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混混,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人兴奋地挥舞着锄头,
叶老四的儿子刚考上高中,此刻正举着根木棍大喊大叫,
额头上还沾着块泥巴;有人则面露惧色,村东头的王寡妇悄悄往人群后缩,
她男人十年前跟人打架被判刑,家里就剩她和个小闺女。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狠辣的叶照,
那个平时沉默寡言,总爱坐在祠堂门口抽烟的男人,那个在狱中磨砺了二十年的男人,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少年。黎明时分,天边刚泛起鱼肚白,
警车的鸣笛声就划破了村庄的宁静。那声音由远及近,尖锐得像锥子,扎得人心里发慌。
陈警官带着几名警员走进村子,他穿着件深蓝色的警服,领口被雨水打湿了一片。
目光扫过地上的血迹和狼藉的战场,眉头皱成了川字,像被揉皱的纸。"叶照,你又惹事了?
"他蹲下身查看"疯狗"的伤势,手指碰了碰对方脸上的伤口,那口子深可见骨,
肉都翻了出来。"这下手也太狠了,都快把人半边脸削下来了。"他的声音里带着无奈,
这个村子的事,像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叶照站在祠堂台阶上,
晨光为他镀上一层血色的轮廓。他的头发被雨水打湿,贴在额头上,
露出那道从眉骨延伸到下颌的伤疤,此刻在光线下像条暗红色的蜈蚣。"陈警官,
我这是自卫。"他的声音不卑不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金牙彪要灭我满门,
我总不能伸着脖子等死。"然而,村子里的气氛却愈发紧张。叶明辉站在人群中,
举着手机对着地上的伤者拍照,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看看!
这就是你们选的族长!"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刻意的煽动。"非要把我们村子拖进火坑!
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只有这样,金牙彪才会放过我们!"他边说边往后退,
眼睛瞟着村口的方向,像是在等什么人。七叔公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出来,
拐杖头在地上戳出个小坑。他浑浊的老眼瞪着叶明辉,眼里的光却像燃着的炭火。
"当年金牙彪占我们田地的时候,你怎么不喊报警?"老人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掷地有声。
"你还帮着他们丈量土地,得了两袋白面!现在村子有难,你倒成了缩头乌龟!"他顿了顿,
拐杖重重一捣,"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叶照做得没错!"人群里炸开了锅。
有人附和七叔公,说金牙彪就是欺软怕硬;有人却小声嘀咕,说叶照太冲动,
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阿霞嫂抱着刚醒的儿子,孩子还在抽噎,额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话来。陈警官看着剑拔弩张的村民,
叹了口气。他从警二十多年,太清楚这种宗族矛盾背后的复杂性,像团缠在一起的蛇,
分不清谁咬着谁。"叶照,跟我回警局做个笔录。"他拍了拍叶照的肩膀,
掌心的温度透过湿透的衬衫传过去。"记住,再怎么说,私自斗殴是违法的。
"叶照转身走进祠堂,神龛前的油灯还亮着,灯芯结了个大大的灯花。
他在祖宗牌位前默默伫立了片刻,牌位上的名字有些已经模糊,是被岁月和香火熏的。
最上面那块写着"叶氏始祖"的牌位,边角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木头纹理。
他想起昨夜写的遗书,藏在第三排左数第五个牌位后面,
那里的砖是松的;想起藏在族谱夹层里的账本残页,
上面记着金牙彪给"李科长"送了三箱茅台,日期是上个月十五。金牙彪不会善罢甘休,
那人睚眦必报,当年为了弟弟的死,能等二十年,现在受了这奇耻大辱,只会变本加厉。
警方的介入看似能平息事态,实则可能让局面更加复杂——金牙彪背后的人,
小说《族长的遗书》 族长的遗书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