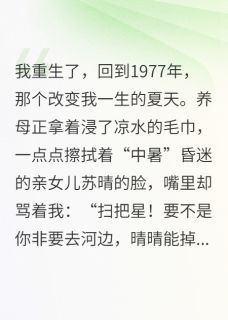精彩小说《桃李成劫》,由佚名创作,主角是张涛李娟。该小说属于[标签:类型]类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细节描写细腻到位。桃李成劫是一本令人欲罢不能的好书!扑通扑通接连跪了下去。十几颗年轻的头颅深深垂下,肩膀剧烈地耸动,压抑的呜咽声被窗外狂暴的雨声粗暴地掩盖、撕碎。那一刻,仿……
《桃李成劫》 桃李成劫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雨点砸在办公室蒙尘的玻璃窗上,留下浑浊的水痕。窗框接缝处洇开一圈深褐色的锈迹,
像一道无法愈合的陈旧伤口,沉默地浸染着灰扑扑的墙壁。
我坐在那张吱呀作响、漆皮剥落的旧椅子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上那份冰冷的文件。
纸张粗粝的触感,带着一种刻薄的硬度。
标题那几个黑体大字——“关于吊销刘志勇特级教师资格证的决定”——如同烧红的铁钎,
狠狠烙进眼底。“作风问题”?我盯着那四个字,几乎要笑出声来。
喉头滚动着铁锈般的腥甜,终究没发出一点声音。眼前晃动着王大海那张油滑的脸,
他经营的“启航教育”培训中心,曾开出天价挖我过去当“门面”。被我拒绝后,
他眼底那瞬间闪过的阴鸷,此刻回想起来,竟成了这场荒唐指控最清晰的注脚。
几张角度刁钻、模糊不清的所谓“暧昧照片”,
几个捕风捉影、语焉不详的所谓“当事人陈述”,
就轻易碾碎了我二十多年粉笔生涯积攒下的全部声名。教育局那位领导合上决定书时,
那声轻飘飘的“老刘啊,影响太坏,先避避风头”,像一根细针,
精准地扎破了维系尊严的最后一点空气。窗外的雨声更急了,哗啦啦地响成一片,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我这荒谬的“落幕”奏响嘈杂的哀乐。
办公室的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条缝,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廉价洗衣粉的气息涌了进来。
十几个身影,像一群受惊的雏鸟,瑟缩着挤在门口狭窄的光线里。他们身上的校服洗得发白,
裤脚和鞋帮溅满了泥点,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角,
雨水顺着年轻却过早显出愁苦的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领头那个瘦高的男孩叫张涛,他父亲在城里打工摔伤了腰,家里塌了半边天。
他死死咬着下唇,嘴唇被咬得泛白,肩膀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他身后,
是更多相似的、带着卑微期盼的眼神。
“刘老师……”张涛的声音像是从被雨水泡透的棉絮里挤出来的,干涩嘶哑,
每一个字都带着颤音,“求求您……再帮帮我们吧!我们……真的没路走了!”话音未落,
他双膝一软,“咚”的一声重重砸在冰冷的水磨石地板上。膝盖撞击地面的闷响,
在压抑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他身后那群孩子,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扑通扑通接连跪了下去。十几颗年轻的头颅深深垂下,肩膀剧烈地耸动,
压抑的呜咽声被窗外狂暴的雨声粗暴地掩盖、撕碎。那一刻,仿佛有一双冰冷粗糙的大手,
猛地攥紧了我的心脏,用力地揉捏挤压。我看着他们被雨水打湿的、卑微到尘埃里的脊背,
看着地上晕开的一小滩一小滩水渍——那是雨水,也是少年们走投无路的绝望。
胸腔里那点因冤屈而燃起的愤怒和自怜,被这沉重的一幕彻底浇熄了。
一种更深沉、更无力、更庞大的东西沉甸甸地压了下来,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起来!
”我的声音猛地拔高,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带着一种近乎撕裂的沙哑,“都给我起来!
”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尖锐刺耳的噪音。我几步冲到门口,
几乎是粗暴地将离得最近的张涛从地上拽起来。手指触到他湿透而冰凉的胳膊,
那寒意直透骨髓。“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跪我做什么?!
”张涛被我拽得一个踉跄,抬起头,脸上湿漉漉一片,眼睛红肿得像桃子。
“老师……我们……我们凑不出复读班的钱……补习班更……更不敢想……”他语无伦次,
声音破碎,“家里……都指着今年……今年……”后面的话,被更汹涌的呜咽堵在了喉咙里。
他身后的呜咽声也大了起来,汇成一片绝望的潮水,几乎要将这间破败的办公室淹没。
我松开他,目光扫过每一张被雨水和泪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脸。那些眼神里有恐惧,有羞愧,
但更多的,是一种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浮木般的、不顾一切的哀求。那眼神像烧红的烙铁,
烫在我的心上。我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弥漫着灰尘、霉味和他们身上带来的、冰冷的雨水气息。再睁开时,
视线掠过桌上那份刺眼的“决定书”,掠过窗玻璃上扭曲流淌的雨痕。“都回家去!
”我挥挥手,声音疲惫得像跋涉了万里,“换身干衣服,别病了。明天……”我顿了顿,
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明天晚上七点,老地方,学校后面废弃的机械厂仓库。
带好你们的课本和卷子。”我几乎是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补充,“钱的事,以后再说。
先把命,给我拼出来!”“老师!”张涛失声叫出来,
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狂喜和更深的惶恐。我没再看他,也没看其他人,只是转过身,
背对着门口那片压抑的呜咽和骤然亮起的、混杂着巨大不安的希望之光。
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被暴雨鞭笞的世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
我把自己仅剩的、摇摇欲坠的一切,都押上了这条注定布满荆棘的绝路。
那扇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隔绝了外面的风雨,却关不住心口那沉甸甸的、冰火交织的重量。
仓库里的空气永远滞重浑浊,
混杂着铁锈的腥气、陈年机油的怪味和几十个年轻身体散发的汗味。
昏黄的白炽灯泡悬在头顶,光线被堆积的废弃机床和蒙尘的杂物切割得支离破碎,
在学生们伏案苦读的身影上投下浓重而摇曳的阴影。这里像一座被遗忘的孤岛,
隔绝了外面那个喧嚣却将他们抛弃的世界。我站在用旧木板临时拼凑的“讲台”前,
粉尘在微弱的光柱里无声飞舞。手中粉笔划过坑洼不平、早已看不出原色的黑板,
发出刺耳的“吱嘎”声。粉笔灰簌簌落下,沾满了我的袖口和指缝,
也落在摊开在破旧课桌上的、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教案本上。那本子边缘早已磨损卷起,
里面的字迹是我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反复斟酌、增删留下的痕迹。“这里,
”我用粉笔重重敲击着黑板上一道复杂的函数题,“核心是数形结合!光背公式没用!
把图像在脑子里给我画活了!”我目光锐利地扫过台下。张涛眉头紧锁,嘴唇无声地翕动,
显然在拼命消化。坐在他旁边的李娟,一个总是怯生生的女孩,
此刻正飞快地在草稿纸上演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急响。汗水沿着她额角的碎发滑落,
滴在纸页上,洇开一小团墨迹。“刘老师……”课间休息时,张涛磨蹭到最后,
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脸上是混合着窘迫和焦虑的复杂表情,
“这……这个月的资料费……我……”他声音越来越低,头也垂了下去。“搁那儿吧。
”我没看他,指了指讲台角落一个敞着口的旧纸箱,
里面已经零星躺了几张同样皱巴巴、面额不一的纸币。纸箱旁边,
是我那个磨掉了漆皮的旧记事本,翻开的那页上,歪歪扭扭地记录着一笔笔“垫付”:张涛,
数学精编,78.5元;李娟,英语真题卷,62元……后面还有一串名字和数字。
那本子沉甸甸的,像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专心做题,别想没用的!
”我语气严厉地打断他可能的道歉,目光却落在他洗得发白、袖口磨破的校服上。
他喉结动了动,最终只是用力地点点头,把那点微薄的钱轻轻放进纸箱,
像放下一个沉重的负担,然后转身快步回到自己那个用砖头垫稳桌腿的座位上,
重新埋首于题海。
黄的灯光下、粉笔灰的飞扬中、旧纸箱里零星增加的纸币和记事本上不断累积的债务数字间,
沉重而飞快地流逝。墙上那张用红笔圈画得密密麻麻的高考倒计时日历,一页页无情地撕去。
倒计时牌上那鲜红的“30天”,像悬在头顶的铡刀,让仓库里的空气绷紧到极限,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铁锈味。学生们的脸上刻满了熬夜的痕迹,眼窝深陷,
嘴唇干裂起皮,但眼神深处却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那是绝望中迸发出的最后一丝凶狠。
我把最后一套亲手编纂、油墨都未干透的“终极押题卷”重重拍在讲台上。
粉尘在灯光下猛地炸开,像一场微型的风暴。“都给我打起精神!最后一遍!
”我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透支后的虚浮,却又异常清晰地在死寂的仓库里回荡,“这套题,
里面的每一道!每一个考点!都是骨头缝里的肉!嚼碎了给我咽下去!”没有欢呼,
没有质疑。回应我的只有一片更加急促的翻页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汇成一片焦灼而充满力量的海浪。张涛的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
额角的青筋因为用力而微微跳动。李娟紧紧攥着笔,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仿佛要将那薄薄的试卷捏碎融入自己的骨血。昏黄的灯光下,那一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庞,
被一种近乎悲壮的专注笼罩着。空气凝滞得如同固体,每一次心跳都清晰可闻。我知道,
押上的不只是他们渺茫的前程,还有我仅存的一切。六月的阳光毫无怜悯地炙烤着大地,
空气中翻腾着热浪。高考结束后的第十天,我那个藏在小巷深处、几乎无人知晓的出租屋门,
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官方冰冷气息的力度敲响了。笃,笃,笃。声音短促、规律,
不容置疑。门开了。刺眼的阳光涌入昏暗的楼道,勾勒出几个穿着深色制服的身影轮廓。
为首的人面无表情地递过一份文件。“刘志勇?跟我们走一趟。
有人实名举报你无证违规办学,非法获利。”他的声音平淡无波,
像在宣读一段与己无关的公告。非法获利?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尖冰凉。
出租屋简陋的书桌上,那个敞开的旧账本像咧开的嘲讽的嘴,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的,
全是触目惊心的赤字——那是我掏空积蓄、甚至借了外债填进去的无底洞。
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血液似乎都凝固了。窗外蝉鸣聒噪,
撕扯着紧绷的神经。法庭肃穆得令人窒息。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旧木头混合的沉闷气味。
高高在上的审判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我孤零零地坐在被告席那冰冷的硬木椅子上,
手心全是黏腻的冷汗。“传唤证人。”审判长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侧门打开。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张涛。他低着头,脚步有些虚浮,不敢看向被告席。他身后,跟着李娟,
还有另外几个我曾耗尽心力去辅导的学生。他们像一串沉默的、被无形的线牵引的木偶,
依次坐上了证人席。法庭里死寂一片,只有他们略显凌乱的脚步声在回荡。“证人张涛,
”控方律师的声音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冷漠,
“你是否曾在被告人刘志勇组织的无证培训班接受辅导?”张涛的头垂得更低了,
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沉默了足有十几秒,
那沉默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最终,
一个细微的、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响起:“……是。
”“你是否向刘志勇缴纳过高额费用?”“……是。”这一次回答得更快,也更模糊,
带着一种急于完成的狼狈。律师满意地点点头,转向审判长:“审判长,
这足以证明被告存在组织行为及牟利事实。请允许我继续询问其他证人。
”律师的目光转向了证人席上那个一直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的瘦小身影——李娟。
“证人李娟,”律师的声音刻意放缓,却带着一种循循善诱的压迫感,“据我们所知,
你的家庭情况非常困难。那么,在刘志勇的培训班里,你是否因为经济原因,
受到了某种形式的不公正对待?或者,被迫接受了一些额外的……条件?”“条件”这个词,
被他咬得格外清晰,带着某种引人遐想的暗示。
旁听席上瞬间响起一片压抑的骚动和窃窃私语。我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一股灼热的怒气和被彻底背叛的冰冷寒意同时冲上头顶。他竟然试图引导出更肮脏的指控!
我几乎要拍案而起,却被身边法律援助律师轻轻按住了手臂,他对我微微摇头,
眼神示意我保持冷静。李娟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像一片在寒风中即将凋零的叶子。
她猛地抬起头,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嘴唇哆嗦着,那双曾经充满怯懦和感激的眼睛,
此刻却死死地、直直地看向被告席上的我。
那眼神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巨大痛苦、挣扎和一种近乎绝望的羞愧。“不……不是的!
”她的声音尖利得变了调,带着哭腔,猛地打断了律师的话,
“刘老师他……他帮我垫了资料费!他……他从来没……”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只能拼命地摇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反对!控方律师在进行诱导性提问!
”我的律师立刻起身,声音洪亮地提出**。审判长敲了下法槌:“反对有效!控方律师,
请注意你的措辞!证人只需回答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客观事实!”他的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
律师的脸色微微一僵,但很快恢复如常,他不再看李娟,似乎觉得这个女孩的崩溃毫无价值。
他转向审判长,语气恢复了那种程式化的冷漠:“好的,审判长。那么,
请证人李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自愿支付了费用,
并清楚知道刘志勇的培训班没有合法资质?”李娟的抽泣声在寂静的法庭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肩膀还在无法控制地耸动。她再次抬起头,这一次,
目光似乎失去了焦点,茫然地望着前方某个虚空点。她的声音轻飘飘的,
带着一种麻木的、认命般的空洞:“……是。我……我知道。”说完,
她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重新深深地垂下了头,散落的头发遮住了她满是泪痕的脸。
律师转向审判长,微微颔首,表示询问结束。
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胜利者的松弛。轮到我的律师进行质证了。他站起身,
走到证人席前,目光平静地扫过张涛、李娟和其他几个学生。
他拿起那份我提供的、记录着每一笔垫付费用的旧账本复印件,
纸张的边缘因为反复翻看而磨损起毛。“证人张涛,”他的声音很温和,
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请你看一下这份清单。第17页,记录着你母亲生病期间,
刘志勇老师替你垫付的三次模拟考试费和**复习资料费,总计584元。
后面还有你的签名确认。这是否属实?”张涛的身体猛地一颤,
像是被无形的鞭子抽打了一下。他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份复印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嘴唇剧烈地哆嗦着。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最终,
他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头颅深深地、几乎要埋进胸口,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压抑的呜咽声从喉咙深处断断续续地溢出。那是一种混合着巨大羞耻和绝望的悲鸣。
律师没有追问,目光转向李娟:“证人李娟,清单第23页,
清楚地记录着刘老师为你垫付的英语听力设备押金和整个学期的习题册费用,共计320元。
后面是你的签名和指印。这是否属实?”李娟没有抬头,
只是发出一声更加凄楚、更加压抑的悲泣,整个人蜷缩在证人席的椅子里,
瘦小的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最后一片枯叶。那悲泣声在肃穆的法庭里盘旋,
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律师转向审判长:“审判长,这份清单以及证人们此刻的反应,
足以证明我的当事人刘志勇老师,从未以办学为名牟取私利。相反,
他是在自身蒙受不白之冤、失去经济来源的情况下,
出于对这群即将失去升学机会的学生的深切同情和不忍,才冒险提供了无偿的帮助,
甚至为此背负了沉重的个人债务!所谓‘非法获利’,纯属无稽之谈!”他顿了顿,
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激愤:“真正需要拷问的,是这些站在证人席上的年轻人!
是什么让他们背弃了在最黑暗时刻向他们伸出援手的人?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沉默,
甚至成为刺向恩师的刀?!”律师的目光如同实质的探照灯,
缓缓扫过证人席上那一张张惨白、布满泪痕和羞愧的脸。法庭里死一般的寂静,
小说《桃李成劫》 桃李成劫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