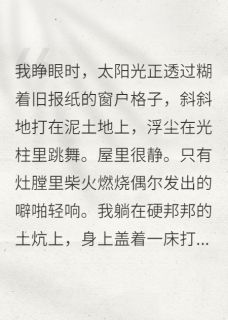《重生七零,我让竹马少奋斗十年》这本书大家都在找,其实这是一本短篇言情小说,是作者卡里多斯的一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陈卫东王红梅,讲述了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村里发生了一件事。村东头赵寡妇家,丢了她男人留下的唯一值钱东西——一块老旧的梅花牌手表。那是她男人当兵……...
《重生七零,我让竹马少奋斗十年》 重生七零,我让竹马少奋斗十年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我睁眼时,太阳光正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格子,斜斜地打在泥土地上,浮尘在光柱里跳舞。
屋里很静。只有灶膛里柴火燃烧偶尔发出的噼啪轻响。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
身上盖着一床打着补丁的蓝布被子,一股子淡淡的霉味混着阳光晒过的味道钻进鼻子。
脑子有点木,像塞满了浸水的棉花。耳边似乎还残留着刺耳的刹车声,
还有陈卫东和王红梅那两张惊慌扭曲、迅速放大的脸。他们当时抱得可真紧,像连体婴。
那辆失控的卡车,直直朝我撞过来。真狠啊。为了抢走我辛苦半辈子打拼出来的公司,
为了抹掉我这个碍事的绊脚石,他们连伪装车祸都敢干。现在……我费力地转动眼珠,
打量这间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
靠墙立着一个掉了漆的木头柜子,上面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磕掉了好几块瓷,
露出底下黑色的铁皮。视线落到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粗糙的红色印刷,上面印着“抓革命,
促生产”几个大字,底下是日期: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我回来了。回到了二十岁,
回到了这个位于北方偏僻山村的知青点。回到了悲剧开始之前。心脏在胸腔里猛地一撞,
随即又被一种冰冷的、沉甸甸的东西压住。不是喜悦,更像是磨刀石压在心头,又冷又硬。
“莫砚,醒了没?该起了!”门外传来王红梅的声音,脆生生的,
带着点刻意装出来的亲热,“再不起,上工要迟到了,李干事又要骂人!”李干事,
管着我们知青点的公社小干部,最是见不得知青偷懒。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那股子土腥味、柴火味,还有属于七十年代特有的、混合着贫穷与亢奋的气息,
真实地填满了肺腑。真的回来了。我掀开被子坐起来,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
炕沿下摆着一双沾满干泥巴的黄胶鞋。脚踩进去,有点硌脚。推开门,
刺眼的阳光让我眯了眯眼。院子里,王红梅正拿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盆在压水井边接水。
她穿着件碎花小褂,两条油亮的麻花辫垂在胸前,脸盘子圆圆的,眼睛弯弯的,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谁能想到,这张甜美的脸皮底下,藏着那么歹毒的心肠。前世,
就是她,在我耳边一遍遍说陈卫东的好,说他多照顾我,多喜欢我,
撺掇着我早早跟他处对象,把回城的机会让给他。最后,更是和他联手,把我推进了地狱。
“砚砚,你可算起来了!”王红梅看见我,立刻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几步走过来,
亲热地挽住我的胳膊,“看你脸色还是不太好,昨儿个淋雨发烧,可吓坏我了。
要不要再歇一天?我去跟李干事说说?”她的手温热,贴在我冰凉的胳膊上。
我只觉得一阵恶寒。前世,就是这种“关心”,让我一步步放松警惕,
把她当成了最知心的姐妹。“不用。”我抽回胳膊,声音有点哑,但很平静,“好多了。
”我走到压水井旁,拿起旁边另一个破盆,用力压下铁把手。冰凉的地下水哗啦啦流出来,
溅起细小的水花。我捧起水,狠狠洗了把脸。冰冷的水**着皮肤,
也让我混乱的思绪彻底冷静下来。王红梅站在旁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似乎有点意外我的冷淡。但她很快又调整过来:“那就好!赶紧收拾收拾,早饭是红薯稀饭,
我锅里热着呢。卫东哥早就在村口槐树下等咱们了。”陈卫东。这个名字像根针,
扎了我一下。前世,他是我们知青点里公认最有“出息”的男青年。脑子活络,嘴皮子利索,
很会来事。尤其会在我面前表现,给我打饭,帮**重活,下雨给我送伞。那时的我,
傻乎乎地以为这就是爱情。他家境比我还差,回城指标更是渺茫。是我,掏心掏肺地对他好,
把家里偷偷寄来的钱票、粮票,省下来大半塞给他。甚至,后来恢复高考,
我熬夜整理复习资料,誊抄得工工整整,全都给了他。结果呢?
他用我整理的资料考上了大学,风风光光回了城。而我,因为把精力都花在了他身上,
自己名落孙山。他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信誓旦旦:“砚砚,你等我,
等我安顿好了就接你进城!”我信了。傻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的,
是他和王红梅在城里结婚的消息。王红梅顶替了她妈的工作,成了城里人。而我,
彻底成了被遗忘在穷山沟里的笑话。再后来,我费尽千辛万苦,像野草一样挣扎着爬回城里,
从最底层的小工做起,摸爬滚打十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小公司,有点起色。
他们又出现了。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陈卫东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地来找我“叙旧”,
诉说着他事业不顺,婚姻不幸(王红梅被他描绘成一个粗俗的泼妇),
怀念我们“纯粹”的知青岁月。王红梅则扮演着被辜负的可怜妻子,
哭哭啼啼找我“主持公道”。我那时竟还对他们存着一丝旧情和怜悯。结果,
换来的就是那辆冲向我的卡车。这对狗男女,榨干了我前世所有的价值,
最后连我的命都要拿走。好。真好。我用力擦干脸上的水珠,抬起头。阳光刺眼,
但我眼神很冷。这辈子,陈卫东,王红梅。你们欠我的,该还了。你们想要的“少奋斗”?
行。我成全你们。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果然站着个人。瘦高个子,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还算结实的小臂。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和又有点腼腆的笑容。陈卫东。他看到我和王红梅走过来,
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快步迎上来,目光直接落在我脸上。“砚砚,你来了!身子好些没?
昨天看你烧得厉害,我担心了一宿。”他语气里满是关切,伸手似乎想探探我的额头。
我微微侧身,躲开了。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王红梅赶紧打圆场,
声音带着刻意的娇嗔:“卫东哥,你看你,眼里就只有砚砚!我都站这儿半天了,
也不见你问我一句。”陈卫东这才把目光转向她,笑容恢复自然:“红梅妹子说哪的话,
这不正要去上工嘛。走吧,再磨蹭真要迟了。”他自然地走到我另一侧,
和王红梅一左一右,像前世一样,把我夹在中间。我沉默地走着,
听着他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队里的闲话,谁家又吵架了,谁家偷偷养鸡被罚了工分。
前世,我觉得这种被簇拥的感觉挺好,说明我人缘好。现在,
只觉得像被两条冰冷的毒蛇缠着。上工的地头离村子不远,是一片苞米地。
绿油油的苞米苗已经有半人高,正是锄草追肥的时候。李干事背着手站在地头,
一张黑黄脸拉得老长,三角眼扫视着稀稀拉拉走来的知青们。“磨磨蹭蹭!
一个个都属王八的?看看日头!还想不想吃饭了!”他唾沫星子乱飞,“莫砚!王红梅!
陈卫东!你们仨,去东头那垄!今天不把这垄草锄完,都别想下工!”没人敢吱声,
各自领了锈迹斑斑的锄头,闷头钻进一人多高的苞米地里。七月的日头,毒得很。
苞米地里密不透风,像个大蒸笼。汗水瞬间就冒了出来,顺着额头、鬓角往下淌,
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衣服黏糊糊地贴在身上,又闷又痒。锄头很沉,抡起来,刨下去,
带起干燥的泥土和杂草根茎。没干一会儿,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腰也像要断了。我咬着牙,
一声不吭,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手心很快磨得发红,**辣地疼。前世,我娇气,
干一会儿就喊累。陈卫东总会很“体贴”地让我去地头树荫下歇着,说我的活他包了。
王红梅也在一旁帮腔:“是啊砚砚,你身子弱,别累坏了,卫东哥心疼着呢!
”那时我多感动啊。现在想想,真是蠢透了。他替**的活,最终都算在我头上?
工分不会多记,反而让我成了别人眼里偷奸耍滑、靠男人养着的娇**。名声坏了,
回城推荐更轮不到我。“砚砚,你歇会儿吧?”陈卫东的声音从旁边的垄沟传来,带着喘,
“看你脸都白了,汗跟水洗似的。这点活,我和红梅妹子加把劲就干了。
”王红梅也立刻附和:“对对,砚砚你去歇着,这里有我们呢!卫东哥最会心疼人了!
”我停下动作,拄着锄头,抹了把汗,看向他。他脸上也全是汗,工装后背湿了一大片,
眼神殷切,努力做出真诚可靠的样子。我扯了扯嘴角,没笑:“不用。李干事说了,干不完,
都别下工。我自己的活,自己干。”说完,不再看他错愕的表情,弯下腰,继续抡锄头。
锄刃刮过土地,发出沉闷的“嚓嚓”声。一下,又一下。汗水砸进脚下的泥土里。
陈卫东和王红梅面面相觑,显然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砚砚,你……是不是还生着病?
不舒服?”陈卫东试探着问,语气有点小心翼翼。“没有。”我头也不抬。
王红梅眼珠转了转,凑近我一点,压低声音,带着点神秘兮兮:“砚砚,
你是不是……听到啥闲话了?关于卫东哥的?你别信那些人嚼舌根,
卫东哥对你可是一心一意的!他昨天还跟我说,等有机会回城,第一个就……”“红梅!
”陈卫东突然打断她,声音有点急,带着警告的意味,“瞎说什么呢!干活!赶紧干活!
”王红梅被他吼得一怔,委屈地撇撇嘴,不说话了,低头用力锄草,
把气都撒在无辜的杂草上。我冷眼看着他们的眉眼官司。看来,这对狗男女,
现在就已经开始互相试探、互相防备了?或者说,陈卫东现在还没完全信任王红梅,
没把他脚踏两只船、利用我的心思完全透露给她?有意思。我没再理会他们。埋头苦干。
胳膊越来越酸,腰越来越沉,手心磨破的地方钻心地疼。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一股要把前世受的苦、流的泪、流的血,都在这烈日下、在这沉重的锄头下,
一点点砸进泥土里的狠劲。这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比起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被碾碎在车轮下的绝望,这算什么?干!汗水迷了眼,我用袖子狠狠一抹。继续干。
中午收工的哨子吹响时,我负责的那一垄地,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反观陈卫东和王红梅那边,还剩下一小截,草锄得歪歪扭扭,深浅不一。
李干事背着手过来检查,三角眼在我锄过的地和陈卫东他们那边扫了扫,
鼻子里哼了一声:“莫砚,还行。陈卫东,王红梅!磨洋工是吧?下午继续!干不完扣工分!
”陈卫东脸涨得通红,想辩解,被李干事一瞪,又咽了回去,只能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带着不解,还有一丝被驳了面子的恼怒。王红梅更是委屈得眼眶都红了,
小声嘟囔:“明明那么卖力了……”我拎起锄头,谁也没看,径直往知青点走。
午饭依旧是红薯稀饭,配一小碟咸萝卜条。我端着碗,坐在院子角落的小马扎上,默默地吃。
陈卫东端着碗凑过来,挨着我坐下。“砚砚,”他声音放得很低,带着点讨好的意味,
“上午……是我不好,没考虑到你刚病好。下午你别那么拼了,该歇就歇,李干事那边,
我去说。”我咽下一口寡淡的稀饭,没看他:“不用。”他碰了个软钉子,有点讪讪的。
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这次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分享秘密的亲近:“砚砚,
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千万别往外传。”我抬眼看他。他左右看看,确认王红梅在屋里没出来,
才神秘兮兮地说:“我听说……上面可能有风声了,要恢复高考!”我的心猛地一跳。来了!
这就是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关键节点!前世,
这个消息也是陈卫东第一个“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的。然后,
他装作一副忧心忡忡、毫无准备的样子。是我,
傻乎乎地把自己偷偷攒下的、家里寄来的所有有关初高中课本、习题资料都翻了出来,
熬夜整理、誊抄,把自己搞得憔悴不堪,最后全给了他。他拿着我的资料,如获至宝。而我,
因为精力分散,加上资料匮乏,最终落榜。“哦?”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淡淡的,
“听谁说的?靠谱吗?”陈卫东见我反应平淡,有点着急:“真的!绝对靠谱!
我……我在公社帮工,听一个干部悄悄说的!千真万确!砚砚,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啊!
咱们知青回城的唯一指望了!”他观察着我的脸色,试探着说:“可是……你也知道,
咱们下乡这么多年,课本早就丢光了,资料也找不到。唉,
这可怎么办……”他重重叹了口气,眉头紧锁,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前世,
我就是被他这副“走投无路”的样子骗了,立刻拍着胸脯说:“卫东,你别急!我有办法!
我家里以前给我寄过一些旧书,我找找看!”然后,我就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这一次……我慢条斯理地喝完最后一口稀饭,放下碗,才看向他。“是吗?
”我语气平静无波,“那确实是个机会。不过,我课本也早没了,帮不上你什么忙。
”陈卫东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变成错愕和难以置信。“砚砚,
你……你不是有……”他下意识地想说“你不是有那些书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大概意识到自己太急切了。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下午去一趟大队部,
看看有没有废报纸可以糊墙。屋里太潮了。”说完,不再看他那张写满算计和失望的脸,
转身走开。心,在胸腔里跳得沉稳有力。陈卫东,你想要资料?做梦。这一次,那些书,
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下午上工前,我借口找李干事问点事,绕到了大队部后面。
大队部旁边有个堆放杂物的小仓房,门常年锁着,但我知道那锁就是摆设,用力一拽就能开。
前世,
陈卫东就是在这里“偶然”发现了几本被当做废品收来的、破破烂烂的旧课本和习题册,
当做宝贝一样藏了起来,后来成了他复习的重要资料。当时我还傻乎乎地以为他运气好。
现在想想,这“偶然”,恐怕也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他脑子活,消息灵通,
肯定早就瞄上了这里。我左右看看,没人。用力一拽那把锈迹斑斑的锁头。
“咔哒”一声轻响,锁扣开了。推开门,一股浓重的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
里面堆着破箩筐、烂麻袋、坏掉的农具,角落里,
果然散乱地扔着几本卷了边、沾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旧书。我快步走过去,蹲下身,
拂开上面的灰。一本皱巴巴的高中代数,一本物理,一本化学,还有两本薄薄的习题集。
虽然破旧不堪,但里面的内容基本完整!我的心跳得飞快,像揣了个小兔子。就是它们!
我迅速脱下身上的旧外套,把这几本书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抱在怀里。
然后飞快地退出仓房,把锁虚虚地挂回去,尽量恢复原状。抱着这包“宝贝”,
我没回知青点,而是直接绕到了村后山脚下。那里有个废弃的看青人歇脚的小窝棚,
早就塌了半边,平时根本没人去。我钻进窝棚相对完好的角落,
把书藏在一堆干草和破烂瓦片底下,又仔细地掩盖好痕迹。做完这一切,我才松了口气,
靠着冰冷的土墙,慢慢滑坐到地上。手心因为紧张和用力,全是汗。怀里空空如也,
但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有了这些书,就有了希望。更重要的是,陈卫东的登天梯,
被我提前抽走了。下午上工时,陈卫东明显心不在焉,锄草的动作有气无力,
眼神时不时瞟向大队部的方向。王红梅凑在他身边,嘀嘀咕咕,似乎在抱怨着什么。
李干事背着手溜达过来,看到陈卫东那垄地锄得跟狗啃似的,顿时火冒三丈:“陈卫东!
你眼珠子长头顶上了?草没锄干净,苞米苗倒给你撅倒两棵!你存心搞破坏是不是?
扣你两个工分!”陈卫东被骂得抬不起头,脸一阵红一阵白,连声辩解:“李干事,不是,
我……我昨儿没睡好……”“没睡好?我看你是心思没在干活上!再这样,
晚上学习会你第一个做检讨!”李干事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陈卫东唯唯诺诺地应着,
眼神却更加阴郁烦躁。我冷眼旁观,抡起锄头,一下一下,干净利落地锄掉杂草,
留下茁壮的苞米苗。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心里一片冰冷。这才刚开始呢,陈卫东。晚上,
知青点的大通铺上。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挂在房梁上,火苗跳跃,在土墙上投下晃动的人影。
大家累了一天,都瘫在炕上,有气无力地闲聊着。王红梅挨着我,
拿着把破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给我扇着风,声音带着试探:“砚砚,下午你去大队部,
看到啥新鲜事没?”“没有。”我闭着眼假寐。“哦……”她拖长了调子,
“我下午好像看见卫东哥也往大队部那边去了,转悠了半天,也不知道找啥。”我没吭声。
陈卫东果然去了。发现仓房里的书不见了,他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砚砚,
”王红梅凑得更近,声音压得极低,带着蛊惑,“你觉不觉得,卫东哥今天怪怪的?
魂不守舍的。我问他,他啥也不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我睁开眼,
看着她近在咫尺、写满“关心”的脸。“没有。”我淡淡地说,
“可能他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吧。”王红梅愣了一下,眼神闪烁:“重要的东西?啥东西?
”“谁知道呢。”我翻了个身,背对着她,“睡吧,明天还得早起。”身后,
王红梅沉默了一会儿,蒲扇也停了。我能感觉到她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背上。她肯定也在琢磨,
陈卫东到底丢了什么?跟我有没有关系?猜吧。使劲猜。最好你们互相猜忌,狗咬狗。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被拉长的皮筋,缓慢而煎熬。白天是没完没了的农活,顶着毒日头,
弯着腰,在望不到头的田垄里挣扎。汗水浸透了衣裳,又在烈日下烤干,
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手心从红肿到磨出厚厚的茧子,再到被粗糙的农具磨破,渗出血丝,
钻心地疼。晚上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但我心里揣着一团火。
一团冰冷的、复仇的火焰。每天下工,不管多累,我都会偷偷溜去后山的破窝棚。
窝棚里又闷又热,蚊子嗡嗡叫。
我点着一小截从灶膛里偷拿出来的、带着松油味的木柴头照明,微弱的光线下,
摊开那些破旧的书本。灰尘呛得我直咳嗽。书页发黄发脆,字迹模糊不清。代数公式像天书,
物理电路图一团乱麻,化学方程式更是看得我头昏脑涨。很多知识,隔了前世几十年,
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太难了。比抡一天锄头还累。好几次,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
我绝望得想哭,想把书撕了,扔进山沟里。凭什么我要受这份罪?前世被他们害死还不够吗?
这辈子还要在这鬼地方啃这些破烂书本?但一想到陈卫东和王红梅那两张脸,
想到他们前世的风光和得意,想到车轮碾过身体时的剧痛和冰冷……这点苦,算什么?
我狠狠抹掉眼角渗出的生理性泪水,抓起一块捡来的、边缘锋利的碎石片,在窝棚的泥地上,
借着微弱的光,一遍遍划拉着那些公式,那些反应式。不会?那就死记硬背!一遍记不住,
就十遍!一百遍!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又涩又疼。蚊子疯狂地叮咬着**的皮肤,
又痒又肿。我不管。只是咬着牙,瞪着眼睛,死死盯着地上的划痕,嘴里无声地念诵着。
像一个疯子。一个被仇恨和执念驱动的疯子。窝棚外的天色,由昏黄变成漆黑。
山里的夜风带着凉意吹进来。我才合上书本,用干草仔细盖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回知青点。陈卫东和王红梅的状态越来越差。陈卫东像丢了魂。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干活时“体贴”地照顾我(当然,我也不需要)。他变得沉默寡言,
眼神阴鸷,干活时经常出错,被李干事骂的次数越来越多。扣工分,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
他肯定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没找到那些书。恢复高考的消息像块烧红的烙铁,
烫得他坐立不安。没有复习资料,他拿什么去考?回城的希望就在眼前,却像水里的月亮,
看得见摸不着。这种煎熬,快把他逼疯了。王红梅的日子也不好过。
陈卫东的坏脾气都撒在了她身上。她几次想凑上去安慰,都被他不耐烦地推开。她委屈,
又不敢大声抱怨,只能把怨气憋在心里,看向我的眼神也越发复杂,
带着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恨。她大概觉得,陈卫东的反常,一定跟我有关。
知青点里弥漫着一种诡异而压抑的气氛。没人知道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
但那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还是随着时间推移,悄然笼罩下来。
有门路、家里条件好点的知青,开始偷偷托人从城里带书带资料。消息闭塞、家境贫寒的,
只能更加绝望地埋头干活。这天下午,轮到我去公社粮站送公粮。赶着队里的破驴车,
拉着几麻袋晒干的苞米粒,吱吱呀呀地走在坑洼的土路上。回来时,天色有些阴沉,
像是要下雨。路过公社唯一那条有点人气的街口时,我无意间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鬼鬼祟祟地钻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子。是陈卫东!他去公社干什么?还这么偷偷摸摸?
我心头一动,把驴车拴在路边一棵老槐树下,悄悄跟了上去。巷子又窄又深,
两边是高高的土墙,散发着一股尿臊味。我贴着墙根,放轻脚步,探头往里看。
只见巷子深处,
陈卫东正和一个穿着灰色干部服、戴着眼镜、梳着分头的中年男人在低声交谈。
那男人我认得,是公社宣传科的周干事,有点小权,平时总爱摆架子。
陈卫东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点头哈腰,从怀里摸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
飞快地塞进周干事手里。周干事捏了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还拍了拍陈卫东的肩膀。陈卫东千恩万谢,又警惕地左右看看,才弓着腰,快速离开了巷子。
我躲在墙角的阴影里,心砰砰直跳。陈卫东在干什么?行贿?他哪来的钱?前世可没这一出!
看来,没了复习资料,他急了,开始另辟蹊径了?是想通过周干事搞到资料?
还是想提前疏通回城的路子?那个小包里,是什么?我看着他消失在巷口,没有立刻跟出去。
等周干事也哼着小曲走远了,我才走到他们刚才交易的地方,蹲下身,仔细查看。泥地上,
除了几个杂乱的脚印,没什么特别。我正要起身,
眼角余光瞥见墙角一小块被踩进泥里的、暗红色的东西。我捡起来,剥掉泥土。
是一小片揉皱了的、印着红双喜字的糖纸。这种高级水果糖,村里供销社根本没有,
只有公社干部或者城里人才吃得起。陈卫东哪来的钱买这个?我捏着那片糖纸,
冰凉的塑料触感,却像块烙铁烫着我的手心。一个模糊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脑海。前世,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村里发生了一件事。村东头赵寡妇家,
丢了她男人留下的唯一值钱东西——一块老旧的梅花牌手表。那是她男人当兵时得的,
是她家的念想,也是她打算给儿子娶媳妇时用的。表丢了,赵寡妇哭得死去活来,
在村里闹了好一阵,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外村流窜的小偷干的。
小说《重生七零,我让竹马少奋斗十年》 重生七零,我让竹马少奋斗十年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