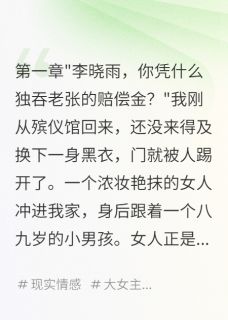关键角色是苏明薇林晚的小说,名字叫做《假千金撕碎全家福后,真千金递刀》,这是一部由作者“临渊城的露琪亚”倾心创作的短篇言情爽文,小说内容介绍:笼子倒是镶金嵌玉的。”那目光像探照灯,**裸地扫过苏明薇身上昂贵的衣裙,扫过她精心护理过的指甲,扫过她脸上无懈……
《假千金撕碎全家福后,真千金递刀》 假千金撕碎全家福后,真千金递刀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我被豪门养了十八年,直到真千金林晚踹开大门。她满身机油味,笑我金丝雀不懂自由。
后来家族逼她联姻,我偷了保险柜钥匙塞进她手心:“飞吧。
”她却撕了机票冷笑:“这群老东西,该尝尝修理扳手的滋味了。
”暴雨夜我们并肩站在祠堂前,族谱在火焰里蜷曲。“合作愉快。
”她沾油污的手与我染蔻丹的手击掌。烧完老宅那晚,
她抛给我一副机车手套:“敢不敢坐后座?
”警笛声中我搂紧她的腰:“油门踩到底——修理费算我的!”雨点砸在玻璃上,
像一群狂暴的囚徒在徒劳地撞击牢笼。又一道惨白的电光撕裂厚重的天鹅绒窗帘缝隙,
瞬间将房间里奢华的轮廓涂抹成狰狞的剪影,旋即被更深的黑暗吞没。轰隆!
雷声紧跟着炸开,震得水晶吊灯都发出细微的嗡鸣。苏明薇猛地从浅眠中惊醒,
心脏在胸腔里撞得生疼。指尖下意识地揪紧了身下冰凉滑腻的真丝床单,
昂贵的埃及棉此刻像一层裹尸布,缠得她喘不过气。喉咙干得发紧,
每一次吞咽都带着铁锈般的滞涩感。她掀开被子,赤脚踩上厚实的地毯,
无声地走向巨大的落地窗。指尖触到冰冷的玻璃,外面是泼墨般倾泻的雨幕,
整个世界只剩下这喧嚣而压抑的水声。床头柜上,手机屏幕突兀地亮起,
幽蓝的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一条新信息,来自那个备注为“父亲”的号码,
简洁得像一则冰冷的讣告:「明薇,准备一下。林晚,明天到家。」林晚。
这个名字像一颗淬毒的子弹,毫无预兆地击穿了苏明薇精心维持了十八年的平静假象。
那个真正的苏家血脉,那个流落在外的、带着一身机油味的“妹妹”,终于要回来了。
一股冰冷的麻痹感从指尖迅速蔓延到四肢百骸,
她几乎能听到某种东西在体内碎裂的细微声响。她僵硬地转身,像个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
走向房间另一侧那间巨大的步入式衣帽间。感应灯无声亮起,
惨白的光线瞬间吞噬了角落的阴影,也照亮了满目琳琅。
一排排高定礼服、稀有皮包、钻石珠宝在精心布置的光源下反射着冰冷而炫目的光。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香氛混合着真皮和雪松木的沉闷气味,奢华得令人窒息。
她的目光掠过一排排挂得整整齐齐的华服,最终落在一件崭新的、缀满碎钻的晚礼服上。
那是为下个月她所谓的“成人礼暨名媛圈亮相晚宴”准备的战袍,一件镶满钻石的金丝鸟笼。
指尖无意识地抚过那冰凉滑腻的衣料,触感让她胃里一阵翻搅。视线有些模糊地移开,
落到旁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挂着一个款式明显过时、边缘甚至有些磨损的旧帆布包。
与周围的珠光宝气格格不入,像误入皇宫的乞丐。她走过去,指尖微微颤抖着,
小心翼翼地拉开拉链。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最底下,压着一块折叠起来的、已经看不出原色的棉布围巾,角落里,
用细密的针脚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薇”字。这是她生母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帆布包上,
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阳光和皂角的廉价气息,
微弱得几乎要被衣帽间里昂贵的香氛彻底吞噬。这微弱的气息却像一根尖针,
猝不及防地刺破了苏明薇紧绷的神经。
一股巨大的、混杂着恐惧、愤怒和无处可逃的绝望猛地冲上头顶。她猛地转身,
几乎是扑向衣帽间中央那个精致的玻璃展示柜。柜子里没有珠宝,
只有一张巨大的、镶嵌在纯银相框里的全家福。照片上,苏宏远——她名义上的父亲,
面容威严,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旁边的继母柳芸,妆容精致,笑容温婉得无懈可击,
眼底却只有一片精心算计的冰寒。穿着昂贵公主裙、被他们簇拥在中间的那个小女孩,
脸上带着被精心教导出来的、符合“苏家千金”身份的得体微笑,
眼神空洞得像一对漂亮的玻璃珠子。那是她,苏明薇,
一个顶替了别人人生的、被豢养了十八年的赝品。虚假!一切都是虚假!
一股无法抑制的暴戾冲垮了理智的堤坝。苏明薇抓起旁边一个沉重的黄铜镇纸,
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向玻璃柜面!“哗啦——!!!
”刺耳的碎裂声在封闭的衣帽间里炸开,无数晶莹的碎片如同冻结的泪珠般飞溅开来,
有几片擦过她**的手臂,划开细小的血痕。她恍若未觉,
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张在破碎玻璃后显得愈发扭曲的全家福。她伸出手,不顾那些尖锐的棱角,
一把将照片从相框里扯了出来。冰冷的玻璃碎片刺痛掌心,温热的液体沿着手腕蜿蜒流下。
她死死盯着照片上那三个笑容完美的人,指关节捏得咯咯作响。然后,双手猛地向两边用力!
“嘶啦——!”刺耳的撕裂声响起。照片上那副其乐融融的假象,从中间被硬生生扯开。
苏宏远威严的半张脸和柳芸温婉的半张脸被彻底分离。中间那个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
则被无情地撕成了两半,空洞的笑容被裂痕割裂,显得无比诡异而悲凉。
她看着手中变成两半的残破照片,身体因为剧烈的情绪而微微颤抖。
掌心的伤口渗出的血珠滴落在华美的地毯上,晕开一小片暗红的印记,
像一朵丑陋而绝望的花。……三天后,苏家那扇沉重的、雕着繁复花纹的乌木大门,
被一股蛮横的力量从外面狠狠踹开,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
门外站着一个人。阳光从她身后涌进来,勾勒出一个瘦削却异常挺拔的剪影。
洗得发白、磨破了袖口和膝盖的工装裤,沾着大片深色污渍的黑色T恤紧紧贴在身上,
勾勒出利落的线条。脚上一双厚重的、沾满泥土和油污的工装靴,
毫不客气地踩在光可鉴人的意大利进口大理石地砖上,留下清晰的污痕。
一头短发乱糟糟地支棱着,几缕被汗水打湿的碎发贴在额角。她的脸很年轻,
五官轮廓带着一种近乎锋利的倔强,皮肤是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健康蜜色,鼻梁挺直,
嘴唇紧抿成一条直线。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明亮、锐利,像淬了火的刀锋,
带着一股毫不掩饰的野性和审视,直直地刺向门内奢华得令人眩晕的一切。
浓烈的机油、汗水和一种难以形容的金属与尘土混合的气息,随着她的闯入,
瞬间霸道地冲散了苏家大厅里常年弥漫的昂贵熏香。
那是一种属于工厂车间、属于轰鸣机器、属于粗糙而鲜活的外界的味道,
带着一股原始的生命力,粗暴地侵入了这个被精心调校过的无菌空间。管家陈伯脸色煞白,
嘴唇哆嗦着,想上前阻拦又不敢,求助似的望向客厅深处。
苏明薇就站在巨大的旋转楼梯中段,身上穿着一条质地柔软、剪裁完美的米白色羊绒连衣裙。
她扶着冰凉的黄铜扶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她看着那个一步步走进来的身影,
看着那双沾满油污的靴子踩脏光洁的地砖,看着那股粗粝的气息搅乱一室的“高雅”,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沉又闷。来了。那个名叫林晚的“真相”,
终于以最蛮横的姿态,闯入了她小心翼翼维持了十八年的世界。“喂!看够没?
”一个带着明显不耐和沙哑的声音响起,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林晚停下脚步,
微微扬起下巴,目光精准地锁定了楼梯上的苏明薇。她双手随意地插在工装裤口袋里,
嘴角扯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弧度,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金丝雀儿?啧,
笼子倒是镶金嵌玉的。”那目光像探照灯,**裸地扫过苏明薇身上昂贵的衣裙,
扫过她精心护理过的指甲,扫过她脸上无懈可击的妆容,最终落在她略显苍白的脸上。
那眼神里没有嫉妒,没有怨恨,
只有一种近乎刻薄的、对“易碎品”的打量和一种深不见底的疏离。
苏明薇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她强迫自己挺直脊背,指甲更深地掐进扶手里。
金丝雀……这个称呼像一根刺,精准地扎进了她心里最隐秘的痛处。这时,
苏宏远和柳芸才从二楼的走廊现身。苏宏远穿着一丝不苟的深色西装,
脸上是惯常的、滴水不漏的威严,只是眼神深处掠过一丝极快的不悦和审视。
柳芸则穿着一身柔和的香槟色套装,
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混合着震惊、心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的复杂表情。“晚晚?
我的孩子!你……你怎么……”柳芸的声音带着哽咽,快步走下楼梯,
张开手臂想要拥抱林晚,姿态完美得像排练过无数次。林晚在她靠近的瞬间,
却像躲避什么脏东西似的,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动作利落得带着防备。
柳芸的手臂尴尬地僵在半空中。“别碰我。”林晚的声音很冷,像淬了冰渣子。
她甚至没看柳芸那张精心描画过的、泫然欲泣的脸,目光依旧带着刺,牢牢钉在苏明薇身上,
仿佛在评估一件即将被取代的旧物。“脏。”这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抽在柳芸精心维护的“慈母”面具上,也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大厅里。
柳芸的脸瞬间褪尽血色,精心维持的表情出现一丝裂痕。苏宏远浓眉紧锁,
低沉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林晚!注意你的态度!这里是你的家!这位是你的母亲!
”“家?”林晚嗤笑一声,那笑声又短又促,充满了荒谬感。
她环视着这巨大、冰冷、处处透着昂贵距离感的空间,眼神里的讽刺几乎要溢出来。“母亲?
”她重复着,目光掠过柳芸僵硬的脸,最终又落回苏明薇身上,
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近乎残忍的了然,“行吧。那这位,就是占了我窝十八年的金丝雀咯?
”她的视线像冰冷的探针,在苏明薇身上逡巡,
从她光洁的额头、微颤的睫毛、紧抿的毫无血色的唇,
一路滑向她扶着栏杆的、微微发抖的手。那目光里没有丝毫新来者的怯懦或讨好,
只有一种置身事外的、近乎冷酷的观察和评估。空气凝固了。佣人们低着头,
恨不得缩进墙壁里。管家陈伯额头上全是冷汗。柳芸的脸色由白转青,
手指无意识地绞紧了衣角。苏宏远的面色彻底沉了下来,眼神变得极其危险,
像暴风雨前的低压。苏明薇站在楼梯上,感觉自己像一件被放在拍卖台上的瓷器,
被林晚的目光一寸寸地审视、估价。那目光里没有仇恨,却比仇恨更让她感到寒冷。
那是一种彻底的漠然,
一种对“苏明薇”这个身份、这个位置、以及她这十八年人生的彻底否定。
她感觉自己精心构筑的世界,正在这个浑身机油味的闯入者冰冷的目光下,无声地崩裂。
……苏家庞大而冰冷的宅邸,像一个巨大的、运行精密的机器。林晚的归来,
如同一颗粗糙的、带着棱角的石子,被粗暴地投入其中,
瞬间激起了混乱的漩涡和刺耳的摩擦声。
她拒绝搬进二楼那间早已为她准备好的、奢华程度仅次于主卧的“公主房”,
反而径直走向一楼最偏僻、靠近后花园工具房的一个狭小佣人房。管家陈伯急得满头大汗,
几乎要跪下来哀求:“大**,这、这万万使不得啊!这房间又小又潮,
怎么能让您……”“就这儿。”林晚的声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她推开那扇漆皮剥落的旧木门,里面只有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一个掉了漆的旧衣柜,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消毒水残留的气息。她却像是很满意,
随手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扔在光秃秃的床板上。“清净。”她扫了一眼外面富丽堂皇的走廊,
补充了一句,语气里满是嘲讽。她的行李简单得可怜,几件同样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和T恤,
几件同样沾着油污的工具——扳手、螺丝刀、钳子,被随意地丢在墙角。
这些格格不入的东西,和房间里简陋的家具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无声的对抗,
嘲笑着苏家无处不彰显的奢华。用餐时间更是成了无声的战场。
巨大的、能容纳二十人的长条餐桌,铺着浆洗熨烫得一丝不苟的雪白桌布,
摆满了精致的水晶杯和银光闪闪的餐具。林晚坐在长桌的一端,位置是新安排的,
象征着她的“回归”。然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套繁文缛节最辛辣的讽刺。
她无视了面前摆放得如同艺术品的七副刀叉,
直接伸手抓起盘子里烤得恰到好处的、淋着黑松露酱汁的小羊排,像啃馒头一样大口撕咬。
浓稠的酱汁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滴落在雪白的桌布上,晕开刺目的污迹。
她端起盛着昂贵勃艮第红酒的水晶杯,仰头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
姿态豪迈得像在喝路边摊的啤酒,然后随意地用沾满油渍的袖子抹了抹嘴。
苏宏远握着刀叉的手背青筋暴起,脸色铁青得像一块生铁。
每一次金属餐具与骨瓷盘轻微碰撞的清脆声响,都像在敲打他濒临爆发的神经。
柳芸则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吃着面前的食物,动作依旧优雅,
但捏着叉子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精心描画的眉头微微蹙起,泄露着极力压抑的嫌恶。
苏明薇坐在林晚斜对面,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小口地切割着盘子里的食物,味同嚼蜡。
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餐桌上弥漫的、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像一张不断收紧的网。她偶尔抬眼,
目光总会不期然撞上林晚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在享用食物时是纯粹的、带着原始满足感的,
但当她的视线扫过苏宏远铁青的脸、柳芸僵硬的动作,或者落到苏明薇身上时,
小说《假千金撕碎全家福后,真千金递刀》 假千金撕碎全家福后,真千金递刀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