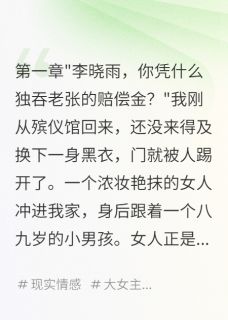小说妓骨的男女主是萧景珩赵岩裴琅,由树七梧栖精心写作而成,扣人心弦,值得一看。小说精彩节选那老鸨就笑得花枝乱颤的迎上前去:「贵客啊哈哈,公子快坐下,我这就叫姑娘出来与您敬酒!」我站起身从屏风后出,端起酒,缓步走……
《妓骨》 妓骨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我是醉月楼最烈的琴妓,用三千曲艳词裹着复仇的刃。新帝一掷千金赎我出青楼时,
不知我袖中金簪淬着灭门毒;他为我挡下太后鸩酒致盲那夜,
亦不知我恨透了他;直到利刃没入他心口,血浸透龙纹——「裴公子,《广陵散》,
我弹与你听」1承平时期,大晟在皇帝萧鉴的统治下,百姓早已不堪重负。
强制征收「养兵税」,农户需交七成收成,拒缴者剁指悬于村口,将其作为罪犯行刑。
由此又衍生出「赎罪银」,交钱可免死,造成地主豪绅抢掠、平民无钱「赎罪」的现象,
人财两空。并且连续五年征十万民夫修筑「通天塔」,死者填入地基,活者交钱出力,
致江淮十室九空。坊间更是流传出「卖小儿以充国库」之说。长此以往,百姓怨声载道,
苦不堪言。承平二十一年冬,三皇子萧景珩亲率边军血洗朱雀门,拿着一把长枪直逼太极殿,
并将太后斩于殿前。次日,先皇退位,萧景珩登基,大赦天下,彼时他年方二十。
但是这与我又有何干系。不过是吃的饭碗里多了几块肉,要赔笑的人更多一些罢了。
2我是一名青楼的清倌人,曾经凭借一曲《血罗衫》走红京城,成了这醉月楼的头牌。
只因我把云氏冤情编入弹词,想借表演之机为父伸冤,却被官府禁演,反而名声更噪。
在我及笄那日,登台前,我如往常一般擦拭我的琴。青楼头牌及笄,这噱头早早被老鸨放出,
许多风流人士竞相登楼。这些人表面上是为听曲,
实际上多是在等着争相竞价青楼头牌女子的初夜。在屏风后,我头戴面纱,
赤足踏上朱红色的地毯,脚上系着金铃铛,一步一响,
耳畔也不断传来丝竹声与杯盏交错的喧闹。在万众瞩目之下,我弹奏了一曲《黍离》。
琴音初起,好似蹒跚老者轻咳,与这喧闹之地格格不入。左手跪指压在琴弦上,
右手滚拂如暴雨打萍。琴声和欢闹声之间,我隐隐听见楼上客房传来的喘息声。不禁想问,
在这烟花之地,只有俯首于这些男人的榻上,才是最后的归宿吗。一曲终,
看着被琴弦割伤的手指,我出了神。老鸨之后又朝着宾客说了些话,逗得台下人欢笑非常。
我一言不发,那些自诩风流的人,已然开始竞价我的初夜,真是令人作呕。
老鸨称「哪位爷竞价成功,姑娘便摇铃敬酒」。竞价声一浪高过一浪,
台下那些人笑得越发放肆,言语越发轻佻。「我出五百两。」「八百两!」「一千二百两!」
……「三千两。」此言一出,厅内顿时鸦雀无声。一位看着富得流油的男子从人群里走出,
脸上带着轻浮的笑容,张口就说:「三千两买姑娘的初夜,姑娘以为如何?」不及我开口,
那老鸨就笑得花枝乱颤的迎上前去:「贵客啊哈哈,公子快坐下,
我这就叫姑娘出来与您敬酒!」我站起身从屏风后出,端起酒,缓步走到那人面前。
厅中人此刻全都目光灼灼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场戏的**。那人伸手与我碰杯,
顺势触摸我的手指,嘴角挂着轻浮的笑容:「姑娘的手,比酒更醉人。」我心底一沉,
抬起酒杯就把杯中酒全倒那人脸上。老鸨大惊失色,连忙道歉,
说让我当众舞一曲《霓裳羽衣曲》向贵客赔罪。我却抽金簪划破衣袖,
当众摘下脚踝上的铃铛,递给老鸨:「这铃铛太贵重,不配我这旧坟里的骨头。
妈妈若是要媚活人,何不自己戴了,去坟头跳给太子看?」那日把老鸨气的不轻,
命人将我关入柴房,呵斥我三日不得进食。站在柴房的窗前,借着月光,
我摩挲着手指上因弹琴过猛而留下的血块。老鸨骂我「罪臣之女装什么清高」,
却不知我恨这曲子。因它曾是太子最喜爱的舞曲,在我父亲被斩之时,
他正坐在东宫听着此曲,享受着他的天伦之乐。3两日过去,在柴房里我饿得差点晕倒,
门外终于传来脚步声。「云姑娘,有贵客指名点你去演奏」,
小丫鬟战战兢兢地为我打开柴房门,向我传话。我有气无力的回:「麻烦和贵人说一声,
稍等片刻。」我撑着墙壁艰难地站起来往外走,
小丫鬟去传完话后急忙跑来将我扶回房间洗漱进食。两盏茶的功夫过去了,
我才推开那间房门。正当我想「又是哪个附庸风雅的俗人」时,只见那人一袭玄色襕衫,
独坐窗边,指尖闲敲棋盘。没有其他客人那缭绕满屋的香薰,也没有油腻的笑脸和夸赞,
他甚至没有抬眼瞧我。我心中升起提防之心,缓步行至琴案前坐下。「公子,可有想听的?」
「《广陵散》。」我猛地按住琴弦,心跳漏了一拍。我从未在人前演奏过《广陵散》,
这首曲子的真本也早已失传,是父亲凭家传古谱将其复原并传授于我,
当今世上除我无人知晓。他是如何得知我会弹?「《广陵散》杀伐气重,姑娘若指力不济,
可换弹其它」,他忽然开口,嗓音冷漠,听不出任何情感。
「父亲曾经和我说《广陵散》需以血润弦,方能弹出磅礴之气。现下我心无志气,
恐怕无法演奏出公子想要的那般。」说罢,我开始弹奏其它曲目,他也不再开口,
只是在窗前摆弄棋局。日光一寸寸地西沉,他的影子从案边爬上我的裙角。屋内未点烛火,
被夕阳照得暗黄,此情此景最易触动人心。不知为何,我的指尖忽然不自觉地转调,
在琴弦上刮擦出嘶哑的泛音——是父亲在家族垂危时,最后教我的一曲《黍离》。
他下棋的指节顿住。明知跪指会磨破手指,我却更用力地压弦,不自觉地加速,如癫狂哭笑,
嘲弄这世间的诸多不公。最后一段本该收得干脆,
尾指却不自觉颤出涟漪——凭什么只剩我一人?曲终了,我抬手抹去不知何时夺出眼眶的泪,
平缓心情。「云姑娘此曲,听着可不像心无志气之人。」窗边人抬眼看我,
他半边脸浸在暮光里似神佛,半边隐于阴影中似修罗,偏偏嘴角又透出一股清流风雅之气。
「不过是想起些陈年往事罢了,若是打扰了公子的雅兴,还请莫怪。」我起身点灯,
并叫房外的丫鬟送些糕点来。对于这人,我心怀疑虑,他好似看穿了我,突然邀我赌棋,
赌注是「一局一问」。我连赢三局,却问不出他的身份——「公子何方人士?」「无家之人。
」「为何听《广陵散》?」「故人所授。」「故人何在?」他收子的手顿了顿:「坟头草,
该有三寸了。」黑子落入棋罐之中,我看见他右手的虎口处,有一凸起的伤疤,
似乎是被何物撕裂后新长出的疤痕。夜深了,窗外的雪飘进房间,落在棋盘上,
我的耳朵也被冻得通红。临走时,他解下大氅扔给我:「**也别冻死了,晦气。」
我反手将其掷进炭盆里,看着貂裘一角烧出青烟,微笑地看着他:「公子,**也嫌脏。」
听我说这句话,他竟不怒反笑:「云姑娘,你父亲教你琴时,可说过‘刚极易折’?」
我装作没听见,转身先他一步离开了房间。后来我才明白,那夜他故意输我三局棋,
是为了引我入局。那件被焚毁的大氅,暗纹里绣着龙纹。而他身上戴着的玉佩,
刻着极小的一个「珩」字。之后他总是隔几日又来一次,行踪莫测,
却每次来就坐在那远离喧闹的包间里,点名让我为他演奏。我也渐渐知道了,他叫裴琅。
4萧景珩以「彻查盐铁走私案」为由微服出巡,而这醉月楼便是盐商最大的据点。
赵前皇后的兄长赵岩等人经常在此密会,萧景珩借听琴之名,安插影卫窃听,搜集证据。
而化名为「裴琅」,不过是权宜之计。我不过是被他蒙骗的一颗棋子,
也如他所愿的入了这局——我弹琴时指尖沁血,他忽然倾身,捏住我的指尖,
用手帕为我擦去血珠。我不自主的僵住,耳尖泛起莫名的红,他却已松开,
淡淡的说:「下次小心。」他下棋总是故意输给我,我斥他是「下棋都让子的伪君子」。
那天暴雨突至,他撑伞送我回房,我故意踩进水洼溅他衣摆,他却将伞更向我这边倾斜。
雨声嘈杂,他忽然低头,呼吸扫过我的耳垂:「云姑娘再闹,
明日恐怕会谣传……裴某深夜湿衣从你房里出来。」我愣了一下,
戏谑的说:「公子也怕闲话?」「怕你吃亏。」他雪夜伫立窗外,询问我是否多加炭火,
我隔窗讥讽他:「裴公子莫不是想把自己冻死?」深夜他翻窗户进我房间,
只为给我送来一枝梅花。我拿着发簪抵住他的喉咙:「裴公子夜半翻窗,是寻人还是寻死?」
他却忽然握住我的手腕,将簪子转向自己的心口:「瑟儿,你刺这里……才杀得了人。」
床头的烛火闪烁,我看见他眼里的自己——唇色潋滟,眸光颤动,哪里有半分杀气?
从春到夏,由秋入冬,我仿佛已经习惯了与裴琅的相处,会因为见到他而心生喜悦,
会因为见不到而暗自神伤。给他人弹琴时,我一心一意扑在琴音里;只有为他而奏时,
总是不禁分神。我自知与他这般相处,并非长久。直到又至一年寒冬,大雪后十日,
裴琅向老鸨提出为我赎身。因我是精通琴技书画的清倌人,又是醉月楼头牌琴妓。
老鸨将我的赎身价开至六千两,此价可抵地方县令的十年俸禄了。谁知裴琅竟当即应下,
很快将我带出醉月楼。他说他是皇商,家底殷实,花钱赎我,绰绰有余,我信以为真。
那日后,他将我带到了一个小院里,院中种满了许多草药,他说这是裴氏的药圃,
让我安心在那居住。但是我知道,这方小院是前朝太医院的旧址,母亲曾带我来此看病。
由于先帝不满太医院如此遥远,便重划地块,修建新的太医院,而这旧址,就被划到宫外了。
在小院的日子,我过得十分舒心。但是裴琅来见我的频率却渐渐减少了,
他就好像是一个得不到又失不去的存在。5当时萧景珩才登基不足三年,虽然夺得皇位,
太子也因触犯了先皇的制衡之道中毒身亡,
但是以赵皇后为首的太子一党依然在朝廷上只手遮天。萧景珩出生时,
其生母周采女就难产而亡,皇帝认为他命中带煞,将他丢由地位卑微的妃嫔抚养。
而作为太子太傅的云谏,曾暗中为他送药、授琴和教书,萧景珩早已把云谏当作恩师来看待。
云氏因「洞庭商船案」而被抄家时,萧景珩才13岁。他跑到行刑台前,
看着自己的恩师被大刀砍下头颅,心中的怒火愈烧愈旺,
这也成为了萧景珩最后夺位的因素之一。萧景珩上位后,马上安排人去寻找云氏遗孤。
未能救云谏,便拼命救其女,似乎想以此来弥补当年遗憾的自己。第一次私服出巡时,
路过青楼,正巧听了一曲磅礴而又悲哀的《黍离》,被弹奏之人吸引,
又见了她伶牙俐齿护自己名誉的桀骜,便对她产生了兴趣。当晚线人来报,
才发现此女就是前太子太傅云谏的女儿——云瑟瑟。而我竟天真的以为他只是一个皇商,
平日不见人影只因他交易繁忙,需要各地奔波。但是在这小院中,唯独一间屋子,
裴琅不让我进,那似乎是一间书房。每次裴琅回来,他总是会到那书房去待上一会。
我在那间小院安稳的度过了两年,这期间裴琅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但是有次我在房门处,
不慎听见他与侍卫的对话,似乎提到了「洞庭商船案」,因隔得有些远,
余下的也就没有听清。或许是自那时起吧,我对他心中也增加了一层说不清的隔阂。
我云氏就是因为这「洞庭商船案」而遭灭门,多年以来,谁能忘记当晚锥心刺骨的痛?
父亲被砍,将头颅悬于西市整整七日七夜,母亲殉情,兄长惨遭炮烙之刑,家中男丁斩首,
女眷全部充入教坊司。在教坊司多年,我见惯了宫中各种人虚伪的嘴脸。
看着各位歌女舞姬为了博得太子青睐,
将《霓裳羽衣曲》跳到脚底磨破也在所不惜;有的人死后美名加身,
有的人活着还是成为他人嘴里的畜生。父亲生前最喜欢读《楚辞》,为我取名「瑟瑟」,
也是出自《楚辞》中的「洞庭波兮木叶下」,寓其澄澈如秋。可是如今,
我已是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曾经那个澄澈的云家女在那一夜已经随父母而亡了。
初入教坊司时,我尚且才9岁,因年纪小而被编入「浣衣局」。每日浆洗贵族华服,
手指经常皲裂溃脓,曾还因洗坏一件织金裙被罚跪雪地。自那以后,每逢深冬,
我的膝盖总是不自觉地隐隐作痛,落下了病根。承平十六年,太子风头正盛,
数不清的宫女贵人都想要爬上他的床榻,只为将来太子登基,能带自己飞黄腾达。
那年我因容貌出众,被教坊使选中练习《霓裳羽衣曲》,我不愿意跳,就用铁链锁住我的脚,
逼我练舞。而后两年,醉月楼老鸨崔氏贿赂教坊使,挑选「有才无色者充官妓,
有色有才者入私坊」。我因通晓诗书被列为「上等货」,标价三百两白银,入醉月楼。
交易当日,我咬伤了老鸨的手臂,被灌哑药三日不能开口。那年我13岁。
在醉月楼接受了两年教习以后,我开始在醉月楼挂牌,凭借琴技,
在一年之内就成为了名东京城的头牌,才发生了后来的事。……入夜,
几道闪电伴随着巨大的雷声,暴雨顿时降临。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想起书屋的屋顶有些漏雨,便起身走出门,却看见裴琅站在廊上看着天。
我走到他身侧:「裴公子,怎的还不睡?」裴公子这个称呼喊惯了,
现下我与他的关系早已不似当初,但我还是喜欢这样喊他。他低头把我搂入怀中,
**在他的胸前。透过他的胸腔,想要听见他没有向我说出的秘密。「瑟儿,我好累。」
「怎么了,可愿和我说说?」我很少见到他这般疲惫的跟我倾诉自己累,
好像他是个永远都胸有成竹的人。在嘈杂的雨声中,他顿了许久,才开口:「没什么,
就是最近遇到的货商都难缠得很,惹人心烦。」我知道,他还是不愿意对我说实话。
雨势渐小了,他将我抱回卧房,让我早些睡觉,但我却透过窗户看见他,
自己走入书屋整理那些不慎被淋湿的书。6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藏得再深的秘密也总有被发现的一天。景珩三年秋的一个夜晚,裴琅原在书房内办公,
突然被侍卫叫出,急匆匆地离去。书房内烛火未熄,门也未落锁。秋日天气干燥,
一阵秋风刮来,竟把书房案上的烛吹翻,火苗舔舐着桌上的文书,书房里传来的烧焦的气味。
情急之中,我来不及穿上外衣,赶忙跑到井边打水救火。幸而火势不大,
仅仅烧焦了书案一角。当我想要整理留存的文书时——「洞庭案·云氏」
五个朱砂字刺入眼帘。我心中突然有一口气堵着说不出来,颤抖着双手打开这份文书。
「臣云谏勾结废太子,私运生铁、盐引至北狄,意图谋反……供认不讳。」
我的指甲掐入掌心,血珠滴在「云谏」的署名上,晕开宛如泪痕。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伪造的认罪书,因为我们云家人写「铁」字总会少一撇,作为防伪证据。
小说《妓骨》 妓骨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