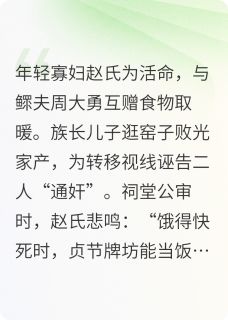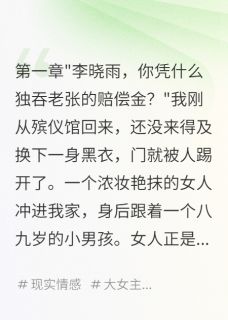《封建时代之沉塘》中的人物设定很饱满,每一位人物都有自己出现的价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引出了周大勇赵守礼的故事,看点十足,《封建时代之沉塘》故事梗概:她却感觉不到冷。方才被托住的手臂处,那残留的触感和温度,像烙印一样清晰。碗里的热气熏着她的眼睛,视线迅速模糊了。她低下头……。
《封建时代之沉塘》 封建时代之沉塘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年轻寡妇赵氏为活命,与鳏夫周大勇互赠食物取暖。族长儿子逛窑子败光家产,
为转移视线诬告二人“通奸”。祠堂公审时,赵氏悲鸣:“饿得快死时,
贞节牌坊能当饭吃吗?”沉塘当日,她最后看到阳光刺穿水面,岸上村民正讨论晚饭吃什么。
---初冬的霜,比刀子更锋利,早早凝在村东头那条瘦骨嶙峋的小河上。河水冰凉刺骨,
赵氏蹲在河边一块凸起的青石上,双手浸泡在水里,揉搓着几件单薄的旧衣。
那水冷得如同淬了寒铁,针扎般钻进她皲裂的指缝,冻得骨头缝都发出无声的**。
她瘦削的肩膀缩着,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卷走的枯叶,脸颊冻得发青,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
腹中火烧火燎的空虚感,一阵紧过一阵,搅得眼前阵阵发黑。她咬紧牙关,
手指在粗硬的布料上机械地搓动,指节冻得通红肿胀。日子仿佛也被冻僵了,一天长似一天,
自打男人在开春一场急病里撒手人寰,只留下几亩薄田和两间漏风的土坯房,
日子便沉入了冰冷的深渊。夫家宗族那些叔伯,当初分走田产房契时的手脚倒是利索,
口口声声“孤儿寡母不易”,转眼间却只余下这刮锅底都嫌薄的“照拂”。
她像秋后被遗忘在枝头的一颗干瘪果子,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默默消耗着最后一点水分。
“哗啦”一声水响,不远处传来嬉闹。赵氏抬起沉重的眼皮望去。
族长赵守礼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赵金宝,正和几个流里流气的青皮后生,
在河边浅水处拿石头砸薄冰取乐。赵金宝裹着簇新的厚棉袍,跺着脚,
呼出的白气里带着一股隔夜的酒气:“哈!脆!真他娘的脆!
跟砸碎那小寡妇的骨头一个响儿!”旁边几个哄笑起来,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浪荡的笑声刀子一样刮过河面。赵氏的心猛地一抽,像被冰水狠狠浇透。她迅速低下头,
将脸埋得更低,恨不得把自己缩进那堆湿冷的衣物里,躲开那些刀子似的目光和话语。
指尖的刺痛和腹中的绞痛搅在一起,眼前一阵阵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青石又冷又硬,
硌得她膝盖生疼。她强撑着搓洗,手臂却越来越沉,每一次抬起都耗尽力气。
冰冷的河水似乎吸走了她最后一点热气,身体深处那点微弱的暖意正一点点消散,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冷和饿。终于,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她眼前猛地一黑,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一倾,整个人就要栽进那刺骨的河水里。
一只粗糙有力的大手及时伸了过来,牢牢抓住了她的胳膊。那手掌很大,
带着常年劳作的厚茧和一种干燥的温热,像一块烧热的石头,瞬间稳住了她摇摇欲坠的身体。
赵氏惊魂未定地抬起头。是周大勇。他不知何时出现在旁边,蹲在稍下游一点的位置,
正沉默地清洗着几个沾满泥土的萝卜。他比她年长些,一张脸被北风和日头刻满了沟壑,
显得格外冷硬,眼神却像冬日午后难得的一点温暾阳光。他身上的旧袄打了好几处补丁,
但还算厚实。“当心点,”他声音低沉沙哑,像砂纸擦过木头,“这石头滑。
”赵氏慌忙稳住身子,脸颊瞬间滚烫,比方才冻僵时还要灼人。她飞快地抽回手臂,
仿佛被那点不合时宜的暖意烫着了,垂着头,声音细若蚊蚋:“……谢、谢过周大哥。
”她不敢看他,只盯着自己那双泡得发白发胀、布满裂口的手,它们在水里微微颤抖着。
周大勇没再说话,只是闷头洗他的萝卜。水声哗啦,气氛凝滞得如同结了冰。过了好一会儿,
他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猛地从脚边湿漉漉的破麻袋里掏出两个沾着泥点的萝卜,
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粗鲁的急切,迅速塞到赵氏还在水里的、盛着湿衣服的木盆边缘。
“洗干净的,”他硬邦邦地说,眼睛只盯着浑浊的河水,仿佛那萝卜是自己跳过去的,
“能顶顶饿。”说完,他飞快地拧干麻袋里最后一点水,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开,
脚步踩在枯草上,发出急促的沙沙声,很快消失在河岸的枯柳树后,
只留下一个沉默而略带仓惶的背影。赵氏呆住了,
看着木盆边那两个沾着水珠、略显笨拙的萝卜。它们还带着河水的湿冷,
却奇异地透出一股属于泥土的生涩气息。腹中的饥饿感骤然变得无比清晰、凶猛,
像无数小兽在撕咬。她盯着萝卜,喉头艰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
岸边似乎还残留着赵金宝他们恶意的哄笑余音,而这两个萝卜,
却像黑暗中突然出现的一星微光。她颤抖着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冰凉的萝卜皮,
那真实的触感让她眼眶猛地一酸。她迅速抓起一个,飞快地藏进湿衣服底下,
心脏在瘦弱的胸膛里擂鼓般狂跳起来,几乎要撞碎她的肋骨。不是为了这微不足道的食物,
而是为了那黑暗中猝不及防递来的一丝微温,
为了那几乎被遗忘的、被当作“人”而非一件碍眼累赘来对待的感觉。那点微温,
在严冬里如同微弱的火星,却足以燎原。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天色灰蒙蒙的,
寒风卷着地上的枯叶打着旋。赵氏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
手里攥着几根刚从自家屋后菜畦边角挖出的、瘦小的地瓜。她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院门,
一眼就瞥见院墙根那块半埋着的、用作垫脚的光滑石头旁,
放着一个用干净旧布包着的小包裹。她的心骤然一跳,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住了。环顾四周,
暮色四合,巷子里空无一人。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快步走过去,蹲下身。
旧布包袱皮洗得发白,散发着淡淡的皂角味。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三个粗面窝头,
颜色灰扑扑的,却蒸得暄软温热,散发着粮食最朴实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窝头底下,
还压着两块拇指大小的、黑乎乎的麦芽糖。腹中的饥饿感瞬间被这香气点燃,
化作一股汹涌的酸楚,直冲上她的鼻尖和眼眶。她认得那包袱皮,
是周大勇常穿的那件旧褂子上撕下来的料子。手指在那温热的窝头上停留了片刻,
感受着那粗糙却实在的触感。她站起身,把窝头和糖重新包好,紧紧抱在怀里,
像抱着一个易碎的暖炉,快步走进低矮昏暗的灶房。她掀开米缸的盖子,
里面只剩一层薄薄的、带着霉味的陈谷底子。她毫不犹豫地将窝头塞进米缸深处藏好,
只留下那两块麦芽糖在掌心。她盯着那两块小小的、深褐色的糖块,
在灶房的幽暗里站了许久。最终,她转身走进里屋,
从那个陪嫁来的、早已掉漆的旧木匣子最底层,摸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支木簪,
样式极简单,没有任何花哨的雕饰,只是被打磨得异常光滑温润,
呈现出一种年深日久的、内敛的檀木色。这是她娘当年给她压箱底的物件,虽不值钱,
却是她身上唯一一件还带着点念想和暖意的东西。她将木簪紧紧攥在手里,
感受着那熟悉的、圆润的弧度,仿佛能汲取到一点点早已消散的母亲的温度。然后,
她转身出了门,趁着夜色渐浓,快步走向村西头。周大勇那两间孤零零的土屋,
就在村外打谷场边,背靠着黑黢黢的山影。院门虚掩着。赵氏在门外站定,
深吸了几口带着寒意的空气,胸腔里那颗心依旧跳得又急又乱。她鼓足勇气,
轻轻推开一条缝。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声掠过光秃秃的树枝。
她一眼看到靠墙放着的、周大勇平时担水用的旧木桶。她飞快地走过去,
将那支温润的木簪轻轻放在了桶沿内侧一个不起眼的凹处,确保它不会轻易掉下来。
做完这一切,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迅速退出门外,拉上院门,
头也不回地没入了沉沉的夜色里,只留下那支带着她掌心余温的木簪,
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木桶上。寒流来袭,北风卷着碎雪粒子,抽打在脸上像砂纸打磨。
赵氏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身上盖着唯一一床又薄又硬的旧棉被,依旧冻得牙齿格格打颤。
白天去河边洗衣服时着了凉,此刻头重脚轻,浑身骨头缝里都往外冒着寒气,
一阵阵发冷后又滚烫起来。灶膛冰冷,缸底那点谷子早已见了底,藏着的窝头也吃光了。
饥饿和寒冷像两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她,越收越紧,意识都有些模糊。就在这时,
院门被轻轻叩响了,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赵氏挣扎着撑起沉重的身体,
扶着冰冷的土墙,一步一挪地走到门边。她费力地拉开沉重的门闩,
刺骨的寒风立刻卷着雪沫灌了进来,激得她一阵猛咳。门外站着周大勇。
高大的身影几乎堵住了狭窄的门框,肩上、头顶落了一层薄薄的雪。他手里端着一个粗陶碗,
碗口用另一只碗倒扣着盖住,但依旧有丝丝缕缕的热气顽强地从碗沿缝隙里钻出来,
带着一种勾魂摄魄的食物香气。那香气混在冰冷的空气里,霸道地钻进赵氏麻木的鼻腔。
是姜汤。浓烈的、辛辣的姜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荤油的独特香气。周大勇没说话,
只是把那粗陶碗往前递了递,眼神落在她烧得通红的脸上和单薄得如同纸片的身子上,
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赵氏喉咙堵得厉害,想说句什么,
却只发出一串压抑不住的、剧烈的咳嗽。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一阵眩晕袭来,她站立不稳,
下意识地伸手去扶门框。周大勇眼疾手快,几乎是本能地往前跨了一步,
空着的那只手迅速而有力地托住了她摇摇欲坠的胳膊。隔着单薄的旧夹袄,
他手掌的温度和力量清晰地传递过来,像一块烙铁,烫得赵氏浑身一颤。她猛地抬头,
正撞进他带着担忧和某种复杂情绪的目光里。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
门外是呼啸的北风和漫天碎雪,门内是冰冷的绝望。唯有两人接触的地方,
那一点支撑的力量和碗中袅袅升腾的热气,成了这冰封世界里唯一真实的存在。
赵氏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周大勇手臂肌肉瞬间的紧绷。
那眼神里的东西太复杂,有担忧,有窘迫,还有一种猝不及防被撞破的慌乱。
“我……”周大勇像是被那眼神烫着了,猛地松开了手,
托着碗的手也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碗里的姜汤晃荡着,差点泼洒出来。
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干涩,“趁热喝了……发汗。”他飞快地把碗塞进赵氏手里,
仿佛那碗是什么烫手的山芋,然后几乎是落荒而逃,
高大的身影迅速消失在风雪弥漫的夜色中,只留下门框边几点迅速被雪覆盖的脚印。
赵氏捧着那碗沉甸甸的、滚烫的姜汤,呆呆地站在门口。寒风卷着雪花扑打在她脸上,
她却感觉不到冷。方才被托住的手臂处,那残留的触感和温度,像烙印一样清晰。
碗里的热气熏着她的眼睛,视线迅速模糊了。她低下头,看着粗陶碗里深褐色的汤水,
上面还飘着几片老姜和一点珍贵的油花。她慢慢地、小心地,把碗凑到嘴边,
浅浅地啜饮了一口。辛辣滚烫的液体滑过喉咙,落入冰冷刺痛的胃里,一股暖流瞬间炸开,
迅速蔓延至冰冷的四肢百骸,连带着那颗被冻僵的心,
也似乎被这猝不及防的温度烫得蜷缩了一下,继而剧烈地搏动起来。她靠在冰冷的门框上,
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碗救命的姜汤,风雪在门外肆虐,而门内,
只有碗沿上氤氲的热气和她压抑不住的、无声滚落的泪水。
日子在饥饿、寒冷和那点隐秘的温暖交换中,如同冰封河面下的暗流,
缓慢而无声地向前淌去。赵氏愈发清瘦,但眼睛里那点将熄的微光,
却因着周大勇隔三差五、沉默地放在墙根石头下的食物——有时是几个蒸熟的土豆,
有时是半块杂面饼——而顽强地维持着。她也会在某个起风的傍晚,将省下的一小把盐,
或者补好的一双旧袜,悄悄放在周大勇院外的柴垛缝隙里。那支温润的木簪,
始终插在周大勇略显蓬乱的发髻上,像一枚无声的徽记。转眼到了冬末,
一场倒春寒比深冬更甚。这天午后,天色阴沉得如同泼墨,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屋顶。
赵氏刚在屋后费力地劈了几根湿柴,累得气喘吁吁,腹中那点食物早已消耗殆尽,
一阵阵心悸伴随着眩晕。她扶着冰冷的土墙喘息,
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摸点冻僵的小鱼虾,院门却猛地被撞开了!
门板重重砸在土墙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赵氏吓得浑身一哆嗦,惊恐地抬头望去。
只见族长赵守礼站在门口,一身簇新的深蓝色缎面棉袍,
衬得他那张保养得宜、留着山羊胡子的脸格外阴沉。他身后跟着几个族中孔武有力的青壮,
都是平时在祠堂里跑腿办事的熟面孔。赵金宝也赫然在列,裹着厚厚的皮裘,
脸色却有些异样的苍白,眼神躲闪,不敢与赵氏对视,
嘴角却挂着一丝极力掩饰却又压不住的幸灾乐祸。一股寒气,比倒春寒的风更刺骨,
瞬间从赵氏的脚底板直冲头顶。“好个不知廉耻的贱妇!”赵守礼的声音像淬了冰,
又尖又利,劈头盖脸砸过来。他根本不看赵氏惨白的脸,枯瘦的手指几乎要戳到她的鼻尖,
“光天化日,竟敢行此苟且之事!败坏我赵家门风,污秽祖宗清名!给我搜!
”最后两个字如同惊雷炸响。几个青壮如狼似虎地冲进狭小的院子,直奔那两间低矮的土屋。
“族长!我没有!我……”赵氏扑上去想阻拦,声音因极度的恐惧和冤屈而尖利变形。
“滚开!”一个壮汉粗暴地一把将她搡开。赵氏踉跄着跌倒在冰冷的泥地上,
手掌被粗粝的地面擦破,**辣地疼。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却被另一个汉子死死按住肩膀,
动弹不得。屋里传来翻箱倒柜、砸碎器物的刺耳声响。赵氏的心也跟着那些声响被撕扯着,
碎裂开来。她徒劳地挣扎着,泪水汹涌而出,嘶喊着:“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搜我的家!
”赵守礼背着手,站在院中,像一尊冷酷的石像,对屋内的动静充耳不闻,
只冷冷地俯视着地上狼狈不堪的赵氏,山羊胡子微微抖动:“凭什么?就凭你寡廉鲜耻!
私通外男!证据?哼,今日定叫你心服口服!”话音未落,一个汉子已从灶房里冲了出来,
手里高举着一个粗布小包,正是周大勇装窝头用的那个旧包袱皮!
他脸上带着发现猎物的兴奋,将小包狠狠抖开在赵守礼面前的地上。“族长!您看!
”包袱皮里,赫然是几块早已干硬发黑的麦芽糖!正是周大勇上次悄悄塞给她的那几块!
它们躺在肮脏的泥地上,像被踩碎的污点。“还有这个!”另一个汉子从里屋奔出,
手里攥着一件男人的旧褂子,正是周大勇常穿的那件打了补丁的灰布褂子!
那是上次赵氏在河边洗衣,周大勇见她冻得厉害,硬塞给她说“挡挡风”的。
她一直没舍得穿,小心地叠放在箱底。“人赃俱获!”赵金宝尖着嗓子,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指着地上的糖块和那件旧褂子,脸上是扭曲的快意,“爹!您都瞧见了!这贱妇还敢抵赖?
这就是她和那野汉子通奸的明证!周大勇那穷鬼的东西,怎么会在她箱底?不是私通是什么?
!”赵守礼的目光扫过地上的“罪证”,又落在赵氏绝望惨白的脸上,眼中没有丝毫意外,
只有一种掌控一切的冰冷和厌恶。他缓缓抬起手,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判词:“绑了!
连同那奸夫,一并押往祠堂!开祠堂门,请族老!今日,我赵氏一门,要清理门户,
以正视听!”粗粝的麻绳狠狠地勒进赵氏纤细的手腕,**辣地疼。
她被两个壮汉粗暴地拖拽起来,像拖一捆没有生命的柴禾。她最后一眼看向自己的院子,
小说《封建时代之沉塘》 封建时代之沉塘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