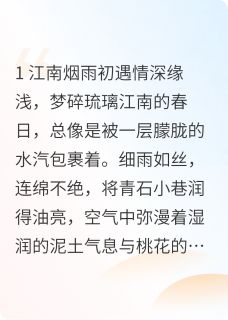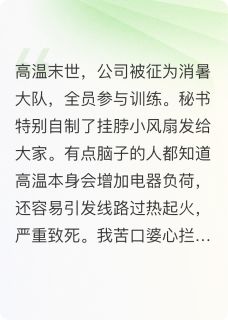《旗袍与病娇》是一部充满爱情与冒险的[标签:类型]小说,由哈里星星精心构思而成。故事中,恬瑜陆子墨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旅程,在途中遇到了[标签:主角的伴侣],二人共同面对着来自内心和外界的考验。他们通过勇敢、坚持和信任,最终战胜了困难,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还是Prada包装的那种。接下来的三天,我闭门谢客,专心做她的旗袍。选了最上等的苏绣真丝,暗纹是昙花——虽然没见过她笑,……将唤起读者心中对爱情和勇气的向往。
《旗袍与病娇》 旗袍与病娇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1我在苏州开了家"任氏手工旗袍店"。每天早晨九点,我推开雕花木门,
阳光斜斜地照在展示架上那些丝缎上,泛起珍珠般的光泽。我点燃一支烟,靠在门框上,
看着游客们从店前经过。"老板,这件旗袍多少钱?
"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女孩指着橱窗里的淡绿色旗袍问道。我吐出一个烟圈,
笑眯眯地说:"姑娘,这件不卖。""为什么?""因为它配不上你。"我掐灭烟头,
走进店里,"我给你量尺寸,做一件专属的。"女孩红了脸。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个穿着盘扣唐装、留着短寸头的男人,手指修长,眼神带钩,
说起话来像抹了蜜。我确实好色,但手艺是真的。祖传的裁缝技艺,加上美院毕业的审美,
让我在苏州旗袍圈小有名气。有钱的太太**们喜欢来找我,一半为了衣服,
一半为了听我讲段子。"任老板,听说你会算命?"女孩怯生生地问。我拿起软尺,
绕到她身后:"伸手。"她乖乖抬起手臂。我的手指划过她的肩膀,
停在腰际:"你五行缺我。"女孩耳根都红了。我笑着记下尺寸:"下周三来试衣,
包你满意。"送走客人,我哼着小调整理布料。突然,门口的风铃响了。
"欢迎光——"我抬头,话卡在喉咙里。一个穿着高定套装的女人站在门口。黑色高跟鞋,
腿长得离谱,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红唇像刚饮过血。她摘下墨镜,眼睛像两颗冰冷的黑曜石。
"听说你是苏州最好的裁缝?"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沙哑。我搓了搓手:"不敢当,
混口饭吃。**想定制旗袍?"她没回答,径直走到店里,
手指拂过一件真丝旗袍:"针脚太粗。"我挑眉:"手工的东西,要的就是这种质朴感。
""狡辩。"她冷笑,"给我做一件,要最好的料子。"我拿出皮尺:"请站好,我量尺寸。
"她没动:"我叫恬瑜。""任平。"我晃了晃皮尺,"恬**,抬手?"她终于配合。
我的手指刚碰到她的肩膀,她就说:"别碰我脖子。""量旗袍必须量颈围。"我解释。
"我说了,别碰。"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危险。我识相地跳过这一步。量到腰时,
她的呼吸明显变快。我假装没注意,但手指不小心碰到她的侧腰——"啊!"她猛地一颤,
然后狠狠瞪我。我无辜地摊手:"意外。"她咬着下唇:"继续。"量完所有尺寸,
我记在本子上:"想要什么款式?""你决定。"她递来一张名片,"做好送到这个地址。
"我瞥了一眼,是苏州最高档的别墅区。名片上只有名字和电话,没有职位。"定金?
"我问。她直接从爱马仕包里掏出一叠现金,估摸有两万:"够吗?""太多了。
"我抽出一半还她。她没接:"剩下的买你闭嘴。"我笑了:"恬**,
我对客人的隐私没兴趣。""所有男人都对我有兴趣。"她转身走向门口,又停下,
"周五前做好。"门关上后,我长舒一口气。这女人像个行走的**包,
还是Prada包装的那种。接下来的三天,我闭门谢客,专心做她的旗袍。
选了最上等的苏绣真丝,暗纹是昙花——虽然没见过她笑,但我觉得她像夜间绽放的花,
美丽而危险。周四晚上,旗袍完工。我发短信问她何时方便送货。回复很快:「明晚七点,
送到云水阁。」云水阁是苏州最贵的餐厅,人均消费够我交半年房租。我咂咂嘴,
把旗袍小心包好。周五傍晚,我换上唯一的西装,抱着礼盒打车去了云水阁。
服务员领我到包厢门口,我敲门。"进来。"是她的声音。我推开门,愣住了。
包厢里不止恬瑜一个人。圆桌旁坐了七八个衣着光鲜的人,主位是个头发花白的男人,
眉眼间和恬瑜有几分相似。恬瑜今天穿了件黑色连衣裙,比上次见面时柔和些。她看到我,
微微点头:"衣服带来了?""是的,恬**。"我递上礼盒。白发男人开口:"这位是?
""爸,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裁缝。"恬瑜接过礼盒,"他的手艺很好。"我这才明白,
这是家族聚餐。而恬瑜让我这个裁缝在这种场合送衣服,显然别有用心。"小伙子,
坐下一起吃吧。"老人和蔼地说。我看向恬瑜,她轻轻点头。我在她旁边的空位坐下,
服务员立刻添了餐具。"任先生做裁缝多久了?"老人问。"家传的手艺,从小学习。
"我回答。恬瑜突然插话:"他还会算命。"桌上的人都笑了。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估计是恬瑜的姑姑——尖声说:"那给我算算?
"我擦擦手:"这位姐姐,你命里缺德。"包厢瞬间安静。恬瑜的嘴角抽了一下。
"开玩笑的。"我笑眯眯地说,"看手相得碰手,我怕姐夫吃醋。"气氛又活跃起来。
老人大笑:"有意思!小任啊,你在哪儿开店?""平江路,小本经营。
"恬瑜突然在桌下踢了我一脚。我吃痛,看向她,她用眼神示意我闭嘴。饭后,
老人被司机接走,其他人也陆续离开。恬瑜拉着我的胳膊:"送我回家。
"她的宾利停在餐厅门口。司机下车开门,恬瑜拽着我坐进去。车内弥漫着她的香水味,
像午夜盛放的玫瑰。我有些局促:"旗袍还满意吗?""没试。"她靠过来,
手指划过我的领带,"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展示你的新玩具?"我半开玩笑。
她猛地收紧领带,我差点窒息:"别自作聪明。我需要一个挡箭牌,你刚好合适。
"我掰开她的手:"为什么是我?""因为你贪财。"她冷笑,"而且不算讨厌。
"车子驶入别墅区,停在一栋三层洋房前。她拽着我下车:"今晚住这儿。
"我瞪大眼:"恬**,我卖艺不卖身。""十万。"她说,"每月。
"我咽了口唾沫:"具体需要我做什么?""陪我出席场合,应付我爸。"她打开门,
"偶尔让我开心。"我跟着她走进豪宅,脑子飞速运转。十万月薪,
相当于我小店半年的收入。"有试用期吗?"我问。她转身,
突然搂住我的脖子:"现在就开始试用。"她的唇压上来,带着红酒的甜香。我本能地回应,
手扶住她的腰。她猛地咬了我的下唇,疼得我倒吸冷气。"这是标记。"她舔掉血珠,
"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我摸了摸破皮的嘴唇,苦笑:"我还没答应呢。
"她走向楼梯:"浴室在二楼,洗干净来我房间。"我站在客厅,环顾这个奢华的牢笼。
墙上挂着她家的合影,我终于认出那个白发老人——苏州最大地产集团的老板。"操。
"我喃喃道,"这下真傍上富婆了。"洗完澡,我穿着浴袍站在她卧室门前。门虚掩着,
我轻轻推开。恬瑜穿着我做的旗袍站在落地窗前,月光勾勒出她的曲线。她转身,
旗袍开叉处露出雪白的大腿。"好看吗?"她问。我点头:"我的手艺,当然好看。
"她走近,手指抚过我的胸口:"知道我为什么选昙花纹样吗?""因为转瞬即逝?
""因为只在夜里绽放。"她解开我的浴袍,"就像我,只在你面前这样。
"我抱起她扔到床上,旗袍皱成一团。她喘息着说:"轻点,这衣服很贵。""我做的,
弄坏了我赔。"我压上去,"用身体赔。"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真心实意地笑,
像昙花一现。事后,她靠在我怀里,手指在我胸口画圈:"明天搬过来。""小店怎么办?
""留着,装样子用。"她打了个哈欠,"我爸不喜欢没事业的男人。"我看着她沉沉睡去,
轻轻拨开她额前的碎发。这个女人像谜一样,危险又迷人。2我被恬瑜的胳膊压得喘不过气。
她睡觉时像个八爪鱼,昨晚那件价值六位数的旗袍皱巴巴地堆在床尾,
像只被抽干灵魂的蝴蝶。我小心翼翼挪开她的手臂,蹑手蹑脚下床。
浴室镜子里的我嘴唇结着血痂,锁骨上还有几道抓痕——这女人连**都像在打架。
手机里有十三条未读消息,全是小店预约客户的抱怨。我正回复着,
背后突然贴上温热的躯体。"谁准你碰手机的?"恬瑜的下巴抵在我肩头,
刚睡醒的声音带着砂纸般的质感。"老板娘,我得维持生计啊。"我转身搂住她的腰,
"不然怎么买钻戒娶你?"她冷笑一声,指甲划过我胸口的伤痕:"十万月薪不够?
""够是够,就是有点费命。"我嘶了一声,"你们有钱人都喜欢在床上玩命?
"她突然掐住我的脖子,力道刚好卡在窒息边缘:"叫我什么?
""老...老板..."我掰着她的手腕,眼前开始发黑。"错。"她松开手,
在我咳嗽时凑到耳边,"叫主人。"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抬头看见她披着丝质睡袍站在晨光里,像个刚完成狩猎的女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这不是包养关系,是驯养。早餐是管家送来的,摆盘精致得像艺术品。
恬瑜用刀尖戳着太阳蛋:"今天陪我去个拍卖会。""我下午有客人..."她抬头看我,
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动物园见过的雪豹:"再说一遍?""我说,旗袍店可以关门。
"我往吐司上抹着鱼子酱,"反正老板娘包养我了。"拍卖会在苏州博物馆的现代展厅。
我穿着恬瑜准备的西装,领口被她用遮瑕膏盖住了咬痕。她挽着我的胳膊入场时,
四周投来的目光像探照灯。"那是恬家独女吧?""旁边的小白脸是谁?
""听说她前男友住院了..."恬瑜面不改色地举牌,
花三百万拍下一幅我看不懂的抽象画。中场休息时,她把我按在洗手间的隔间里,
手指钻进我的衬衫:"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你吗?""因为我帅?""因为你是我的新玩具。
"她咬住我的耳垂,"上一个坚持了两个月,希望你能破纪录。"她的口红蹭在我领口,
像一抹新鲜的血迹。回程车上,恬瑜接到电话,脸色突然阴沉。
挂断后她命令司机:"去平江路。""怎么了?""你的破店着火了。
"远远就看见浓烟滚滚,消防车的警笛声刺破夜空。我的小店烧得只剩骨架,
那些精心收藏的丝绸布料化为灰烬。隔壁茶馆老板跑过来:"任师傅!
幸好你不在里面..."恬瑜站在消防车闪烁的灯光里,黑色大衣被风吹起,
像只振翅的乌鸦。她盯着废墟,突然笑了:"真巧。"我心头一颤:"你干的?
""我要是想毁掉什么,会亲自看着它烧光。"她转身走向车子,"查清楚前,住我那儿。
"那晚她反常地温柔,甚至允许我抽烟。我站在她家露台上,看着苏州的灯火,
突然觉得旗袍店的火光像场荒诞的告别仪式。"难过?"恬瑜从背后环住我的腰。"有点。
"我吐着烟圈,"那是我爷爷传下来的铺子。"她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说:"我十六岁烧过我爸的书房。"我转头看她,月光下她的侧脸像尊瓷器。
"因为他把我养的猫扔了。"她轻笑一声,"后来他再也不敢碰我的东西。"我掐灭烟,
把她转过来面对面:"所以这场火...""不是我。"她眼神突然变得锋利,
"但我知道是谁。"第二天我被门铃吵醒,恬瑜已经出门了。来的是个穿高定西装的男人,
长相和她有七分相似,但眼神油腻得像放了三天的小笼包。"你就是我妹养的小白脸?
"他上下打量我,"品味越来越差了。"我倚着门框笑:"大舅哥吃早饭了吗?
要不要尝尝我下面?"他脸色一沉:"离恬瑜远点,她玩腻的垃圾都是我来收拾。
""包括放火?"男人眯起眼睛:"那只是警告。下次烧的就是你。
"他走后我打电话给恬瑜,响了七声才接通。背景音很吵,像在工地。"你哥刚来威胁我。
"我说,"挺帅的,就是脑子不太好。"电话那头传来金属碰撞声,
恬瑜的呼吸突然加重:"他在你那儿?""刚走。你那边什么声音?""没什么。
"她顿了顿,"今天别出门。"电话挂得突兀。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见小区门口停了辆黑色面包车,两个穿工装的男人正对着我这边指指点点。
恬瑜傍晚才回来,右手缠着绷带,嘴角有淤青。我帮她处理伤口时,
发现她指甲缝里有暗红色的残留。"你哥还好吗?"我问。"在医院。"她抽回手,
"暂时死不了。"我挑起眉毛:"为了我?""少自作多情。"她踢掉高跟鞋,
"我只是讨厌别人碰我的东西。"夜里我被噩梦惊醒,发现恬瑜不在床上。书房亮着灯,
我推门看见她对着电脑屏幕,上面是监控画面——我的旗袍店起火前,
有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门口倒了什么液体。"找到人了?"我走到她身后。
她合上电脑:"明天去香港。""逃难?""购物。"她拉开抽屉,扔给我一本护照,
"你的。"飞机上头等舱的空姐一直对我抛媚眼,
恬瑜在餐巾纸上写了句话推过来:"再对她笑,我就把你从舱门扔出去。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吃醋了?""所有权声明。"她靠在我肩上闭目养神,"睡会儿,
到了有得忙。"香港的酒店套房能看到维多利亚港。恬瑜洗完澡围着浴巾出来,
扔给我一个丝绒盒子。"订婚戒指?"我打开,是把车钥匙。"明天开这辆车。
"她擦着头发,"车牌记住了?
"钥匙上的三叉戟标志硌得我手心发疼:"让我开玛莎拉蒂去撞你哥?""去港口接个箱子。
"她俯身涂乳液,浴巾缝隙间露出腰侧的淤青,"然后等我电话。
"我搂住她的腰:"你到底在计划什么?"她转身跨坐到我腿上,
湿发滴落的水珠打湿我的衬衫:"想知道?"我点头。"那先让我开心。"她扯开我的衣领,
咬在昨天的伤口上,"叫主人。"疼痛混合着**冲上头顶时,我模糊地想,
这大概就是被食人鱼爱上的感觉。3香港的晨光刺进来时,恬瑜已经不在床上。
我摸到枕边有张字条:「十点,车库见。穿黑色。」浴室镜子里映出我锁骨上的咬痕,
像枚紫红色的印章。热水冲下来时,我数了数身上的淤青——五处,比昨天新增两处。
这女人标记所有物的方式真够原始。车库里的玛莎拉蒂是哑光黑的,像头蛰伏的野兽。
恬瑜靠在车边玩打火机,今天穿了件真丝衬衫,衣摆扎进高腰裤里,
腰间若隐若现的淤青让我喉咙发紧。"港口C区12号仓。"她扔来车钥匙,
"接到箱子直接开回浅水湾。""箱子里是什么?"她突然揪住我的衣领,
薄荷烟味喷在我脸上:"再多问一个字,我就把你舌头钉在方向盘上。"车子驶出车库时,
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粒黑点。导航显示到港口要四十分钟,我降下车窗,
咸腥的海风灌进来。港口比想象中荒凉。C区堆满生锈的集装箱,
几个穿工装的男人在阴影里抽烟。12号仓门前站着个戴金链的光头,
脖子上的刺青像条蜈蚣。"任先生?"他咧嘴笑,露出颗金牙。我点头。他做了个手势,
两个马仔推着板车过来,上面是个钢琴烤漆的黑色长箱,大小刚好装得下一个人。"验货?
"金牙问。我摇头,想起恬瑜的警告。箱子被抬进后备箱时,发出沉闷的金属碰撞声。
回程路上电话响了。恬瑜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有人跟着你吗?
"后视镜里空空如也:"目前没有。""甩掉所有尾巴再回来。"电话突然挂断。
小说《旗袍与病娇》 旗袍与病娇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