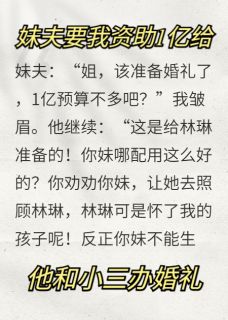由泡泡晓晓编写的热门小说疯人塔里爬出来后,我成了真千金,剧情非常的新颖,没有那么千篇一律,非常好看。小说精彩节选我幼时流落在外,饥寒交迫伤了脾胃,最忌辛辣腥膻之物。沈砚见状,轻轻扶了扶苏挽月的后背,语气带着明显的宠溺与维护:“挽月,……
《疯人塔里爬出来后,我成了真千金》 疯人塔里爬出来后,我成了真千金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我毒害祖母,父兄将我锁进疯人塔。出塔时我格外温顺父兄让我跪我便跪,
让我奉茶我便照做可嫡姐为何抖得比我还厉害?顾神医说过:别人不动刀,我便也不能亮刃。
可我一天没折磨人了,心里痒痒于是月黑风高夜,我鬼魂一般飘到嫡姐床前。
“你何时才肯动手?”匕首插在嫡姐的床头嫡姐瑟瑟发抖是的,我疯了,父兄接我时,
我早就不似从前那般乖张暴戾1“知道错了吗?”“对不起,二哥。是晚照猪油蒙了心,
嫉妒长姐,才会做出那等糊涂事。晚照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的声音微微发颤,
眼眶泛红,早就把提前准备好的话背的滚瓜烂熟果然,沈墨很满意“知错就好,
若非你此次实在过分,长兄也不会将你关入此地。”他顿了顿,“日后,
与你长姐好好相处。”我顺从地,学着苏挽月依赖又柔顺的姿态,
在他的掌心小心翼翼地蹭了蹭沈墨唇角扬起。阴暗处无人注意到,送我出塔的王德海,
紧张的汗珠直往下掉。“沈、沈二公子若是再无吩咐,老奴就不打扰您兄妹团聚了。
”王德海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抖。沈墨点头:“你做得不错。侯府答应的香油钱,
三日内会送到。”“谢、谢谢二公子!”王德海如蒙大赦,忙不迭地躬身行礼,
脚步踉跄着就想往塔里退。“王公公的腿脚,”我忽然侧过头,声音依旧低柔温顺,
像是随口一句无心的感叹,“瞧着真利索呢。”“扑通!”王德海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
肥胖的身体结结实实摔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挣扎起来,手脚并用地冲回了塔里,
“砰”地一声关上了沉重的塔门。沈墨看着他有些诧异,眼中掠过一丝不解“二哥,
”我抬头近乎卑微的表情,“晚照…可以回家了吗?”沈墨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嗯。
”“日后若再敢对你长姐有半分不敬,长兄不同意我也会亲自将你送回此地!”“嗯。
”我乖巧地应着。2忠勇侯府记得半年前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我的“好长姐”苏挽月倚在门内,泪光盈盈声音凄楚又清晰:“晚照妹妹,
你为何要如此狠心?祖母待你如亲孙女,你怎么下得去手?这里是我的家!父亲母亲是我的!
哥哥们也是我的!你算什么东西?”别人的家,我一个外人,怎能擅入?
直到身后的沈墨淡声吩咐:“进来吧。”我脸上小心翼翼的笑容,
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真的…可以吗?”沈墨眼中闪过一丝心疼,但转瞬即逝,
立刻被对我过往“跋扈劣迹”的不悦压了下去。刚踏入前院沈砚朝我走来,
身后跟着的便是苏挽月,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害怕的躲在了沈砚身后“大哥,
我把晚照接回来了。”沈墨上前一步,语气平静地说。沈砚冷漠的看向我,
嫌弃的眼神就像在看什么污秽不堪的东西。“这么快就半年了?”沈砚声音低沉的说快吗?
我在那个不见天日、生不如死的寒窟里度日如年,每一刻都是煎熬,在他们看来,
竟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快”?“才想起来,”沈墨在一旁补充,
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好像还超了三天。
”沈砚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仿佛将我遗忘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里本就是天经地义。我立刻垂首敛目,
双手交叠置于腹前,对着沈砚的方向,深深地、无比恭顺地福下身去。
姿态标准得如同宫中教导嬷嬷手下的典范。苏挽月看见我这副模样,
眼中的惊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盛沈砚感受到她的恐惧,
安抚地拍了拍她紧抓着自己衣袖的手背,目光却如冰锥般刺向林晚照,
声音冷硬如铁:“怕什么?大哥在。她若再敢对你有半分不轨,”他顿了顿,
每一个字都淬着寒意,“下次,我保证,她到死都踏不出那座塔的门槛!”那目光,那话语,
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口。原来,疯人塔里爬出来的人,心,也是会疼的。
“晚照…很乖,很听话的。”我抬起头,迎上沈砚冰冷的目光,眼神清澈无辜,
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惹人怜惜的茫然沈砚嫌恶地别开眼,只护着瑟瑟发抖的苏挽月,
转身向花厅走去:“洗漱,用饭。”4晚膳摆在花厅。琳琅满目,无一例外,
全是苏挽月的口味。苏挽月似乎终于按捺住了心头的恐惧,
她夹起一块裹着厚厚一层花椒碎和茱萸粉的炙鹿肉,轻轻放到我的小碗里。“晚照妹妹,
”她声音轻柔,带着一丝刻意的讨好,“你受苦了,多吃点肉补补身子。”花椒的麻,
茱萸的辣,还有那鹿肉本身浓重的腥膻气——精准地踩在我每一个无法忍受的味觉死穴上。
我幼时流落在外,饥寒交迫伤了脾胃,最忌辛辣腥膻之物。沈砚见状,
轻轻扶了扶苏挽月的后背,语气带着明显的宠溺与维护:“挽月,
你是我忠勇侯府精心教养长大的嫡**,身份贵重,不必对任何人如此低声下气,
更无需刻意讨好!”苏挽月立刻低下头,更显楚楚可怜。我只觉得荒谬。
明明这满桌珍馐皆因她所好而设,明明这府中上下都将她捧在掌心,
为何他们总觉得她苏挽月才是最委屈的那个?
顾悬壶低沉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晚照丫头,记住,在这吃人的地方,
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我乖巧地坐在那里,
目光落在那块红彤彤、油汪汪的烤鹿肉上,喉头急不可耐的滚动了一下,然后,
用一种无比渴望的眼神,小心翼翼地看向沈砚和沈墨:“我…可以吃吗?
”沈砚握着玉箸的手一顿。沈墨端着酒盅的动作僵住。苏挽月扒饭的筷子停在了嘴边,
眼底飞快掠过一丝错愕和几乎压不住的恼恨。一时间,花厅里鸦雀无声。
沈砚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手中的玉箸重重拍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林晚照!
你在这里恶心谁?”他盯着我,目光锐利如刀:“那疯人塔是我忠勇侯府世代捐资修缮,
王德海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苛待于你!”“说谎也要有个限度!
”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当我沈家是摆设不成?”不敢吗?大哥,
你见识过寒窟里钉满铁刺的“清心床”吗?你见过用牛毛细针扎遍周身大穴的“通络术”吗?
你见过为了半个馊掉的窝头,人像野兽一样在泥泞里撕咬翻滚的“斗食场”吗?
沈砚当然没有见识过。但他羽翼下精心呵护的苏挽月,却借着低头掩饰,
唇角无法抑制地向上弯起,若不是极力压制,那笑容几乎要裂到耳根去。我被他的怒火吓到,
猛地站起身,手足无措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头垂得更低,肩膀微微耸动,
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茫然,不敢说一个字。沈墨皱了皱眉,看着我惊弓之鸟的模样,
终究有些不忍,开口劝道:“大哥,今日晚照才回来,我们一家人难得聚在一处,
就不能好好吃顿饭吗?”沈砚胸膛起伏,那股邪火被硬生生压了下去,看向我的眼神,
那份嫌恶却更深重了。沈墨无奈地叹了口气,语气尽量放得温和:“饿坏了吧?多吃点。
”我抬起眼,笑容极其甜美:“谢谢二哥。”沈墨递筷子的手猛地一滞,瞳孔骤然收缩。
他的妹妹……是会这样笑的吗?还笑得如此……干净纯粹?为什么过去的十多年里,
他从未在她脸上见过这样的笑容?原来,只要对她稍微好一点点,
她也是会露出这样甜美的笑容,
用这样甜糯的声音唤他一声“二哥”的……沈砚握着酒杯的手指也几不可察地收紧了一瞬,
眼底有瞬间的恍惚,但那份根深蒂固的成见并未因此改变。5回到我的西厢小院。
房内陈设依旧,我刚想褪下那身散发着霉味的粗布囚衣,房门便被轻轻推开。
苏挽月端着一只白瓷小盅,袅袅娜娜地走了进来。“晚照妹妹,”她声音轻柔,
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怕你夜里睡不安稳,特意给你温了盏安神的牛乳燕窝。我垂着眼,
乖顺地伸手去接:“谢长姐。”苏挽月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笑意更深,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妹妹如今,可真是变了个模样,温顺得叫姐姐都有些不认识了。
”话音未落,她的手猛地一抖!滚烫粘稠的燕窝乳羹瞬间泼洒出来,
大半浇在我刚刚伸出的手臂和单薄的衣襟上,灼热的刺痛感立刻蔓延开来。“哎呀!
”苏挽月惊呼一声,声音里却没有半分真正的惊慌,反而带着一丝得逞的快意,“妹妹,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连个碗都接不稳?”她目光流转,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
落在林晚照被烫红的手臂上。我忍着剧痛没有动,眼神平静无波,
仿佛烫伤的不是我自己苏挽月的目光锁定了窗台上的黄花梨木相框。
那是我早逝的生母给我留下的唯一幅小像。这一次,我动了。
在苏挽月的手即将碰到相框的那一瞬间我牢牢扣住了她的手腕!苏挽月终于得意地笑了,
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地抓起那相框,狠狠朝着坚硬的地砖砸去!“啪嚓!
”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房间里炸响!此刻我胸中翻涌的恨意几乎要冲破理智的牢笼!“哟,
生气了?”苏挽月看着她眼中翻腾的怒火,笑容越发灿烂,带着**裸的的挑衅,“有本事,
你像从前那样,打我啊!”挑衅!顾悬壶沙哑而严厉的告诫如同惊雷在脑海中炸响:“晚照!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你是‘病愈’归来的侯府**!你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话’!忍!
给我忍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听话……”我的指尖狠狠掐进掌心,
剧痛和极致的压抑让我的身体身体微微颤抖。“动手啊!”苏挽月见我不动,反而凑近一步,
声音压低,带着恶毒的蛊惑,“你不是很能打吗?在疯人塔里没打够?在这里,当着我的面,
再打一次试试?看看这次,哥哥们还会不会只关你半年?”“啪——!
”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苏挽月白皙的脸颊上迅速浮现出一个清晰的五指印!
苏挽月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啊——!”她捂住瞬间肿起的脸颊,
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尖叫,“大哥!二哥!救命啊!晚照妹妹又发疯了!
”沈砚和沈墨的身影带着凛冽的寒风冲了进来。“林晚照!你又发什么疯?
”沈砚一把将惊慌失措哭的梨花带雨的苏挽月护在身后我已经收回了手,
重新恢复了那副低眉顺眼的模样,双手规规矩矩地交叠在身前,
声音平静无波:“是她叫我打她的。”苏挽月捂着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呜呜呜……方才我进来送燕窝,
看见妹妹将哥哥们送她的簪子丢进了炭盆!不止如此,她还想撕了姨娘的小像!
我、我上前阻止,她抬手就打我……呜呜呜……”证据确凿。沈墨的目光扫过地上的狼藉,
眼中最后一丝柔软也消失殆尽,只剩下浓浓的失望和疲惫:“晚照,你就这么恨我们,
恨侯府吗?当初你生母早逝,你流落在外,也并非父亲之过,更非侯府之错……”恨吗?
怎能不恨?我在泥泞里挣扎求生十年,寒冬腊月蜷缩在破庙角落,与野狗争食,
为了半个发霉的馒头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而侯府,却将她生母留下的位置,
给了苏挽月这个鸠占鹊巢的替代品,锦衣玉食,千娇万宠!
我怎能不恨你们没有早一点找到我?恨你们将我弄丢了?恨我被弄丢了,
你们就心安理得地找了一个赝品来代替?我更恨每一次都是苏挽月使坏,
你们却像瞎了眼一样,永远坚定不移地站在苏挽月那边!“是我错了,东西是长姐丢的,
姨娘的小像也是长姐砸的……”我从袖中取出疯人塔里顾神医作保的病愈文书,
发誓:“晚照绝无半句虚言!”疯人塔?顾神医?沈墨抢过了那张纸“癔症已除,神志清明,
准予归家。”落款处,还有一个潦草却力透纸背的签名——顾悬壶。沈墨捏着纸的手,
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这…好像是真的……”“顾神医说,我们这些从塔里出来的人,
要乖顺,要听话,才能在这府里……有一席之地。”我认真的说可沈砚一个字也不信。
“乖顺?听话?”他重复着这两个词,眼神锐利如刀,“好!既然你如此‘乖顺听话’,
那现在就立刻搬出这间院子!让挽月住进来!”这间位于西厢、采光极好的小院,
是当年她生母还在时,亲自为我挑选布置的,也是我在这座冰冷府邸中唯一的避风港。曾经,
苏挽月无数次明里暗里想要霸占,我都以命相搏地拒绝了。“好。”我没有任何迟疑,
乖巧地点了点头。转身,开始收拾自己的几件旧衣和几本泛黄的书册。沈砚、沈墨,
连被护在沈砚身后的苏挽月也愣住了。她竟然真的……搬了?苏挽月狂喜,但面上,
她依旧是一副受惊过度的模样,小心翼翼的问沈砚:“大哥,我…我真的可以住这里吗?
晚照妹妹她……”“她都能住得,你为何不能住?”他猛地转头,
目光如冰锥般刺向抱着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的我,手指指向后院最偏僻角落的方向,“以后,
你就睡那里!柴房隔壁的空屋!”我步履轻快地朝着那阴暗潮湿的角落走去,
甚至脚步里还带着点……如释重负?沈砚看着我手脚麻利地清理出一小块地方,
铺上自己带来的、同样单薄的被褥。他感觉,自己胸腔里那股无处发泄的邪火,
几乎要将他整个人点燃、爆炸!他怒极反笑,看着我倒头就要躺下,再次厉声开口:“慢着!
”我抱着被子,茫然又顺从地看向他。下一秒,一个粗使婆子端着一盆冷水,哗啦一声,
泼在了我的被褥上!“这下,”沈砚面色无波,“可以睡了。”我轻轻地吁了口气,
直挺挺地躺进了冰水浸透的被窝里。不过片刻,鼾声响起,我睡得无比香甜。沈砚:“……!
!!”6“……这到底是多久没睡过安稳觉了,
睡了快十个时辰了……”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舒适的床榻上,
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晚照,你醒了?感觉如何?是不是真的……”沈墨关切的问我,
那个“疯”字在他舌尖滚了几滚,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我是从疯人塔里出来的,
但我一点不自卑。”我平静清晰的回答沈墨被我噎得哑口无言,眼眶泛红,低下头,
不敢再看我我歪着头,笨拙地、轻轻地,在沈墨低垂的头顶拍了拍。“二哥,我会听话的。
”沈墨的身体猛地一僵,反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哽咽在喉咙里:“暖暖…是二哥对不起你…以前…是二哥错怪你了…”我只是安静地看着他,
没有任何怨怼,也没有任何动容。沈砚的身影出现在客房虚掩的门外,
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沉沉地压着,闷得喘不过气。最终,那一步,他还是没能踏进去。
7接下来的日子,沈砚陷入偏执的试探。他让我往东,我便绝不往西一步。
他甚至命人捉来我幼时最惧怕的、色彩斑斓的毒蜥蜴,放在我摊开的掌心。
我抖得如同风中落叶,却硬是咬着牙,不敢将那丑陋的活物甩下去。
沈砚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终于有一天,他屏退左右,只留下苏挽月:“挽月,
那支簪子和小像……当真不是你做的?”苏挽月何曾受过这种质疑?
这种委屈瞬间让她红了眼眶,泪水如珍珠滚落。“大哥!”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沈砚脚边,
仰起头,泪眼婆娑,声音凄楚欲绝,“连您…连您也不相信挽月了吗?挽月在您身边长大,
何曾有过半句虚言?
那簪子…那簪子或许是妹妹自己失手打翻的…小像…小像…呜呜呜……”她泣不成声,
仿佛受了天大的冤屈,“若大哥疑我,挽月…挽月这就绞了头发去做姑子!
也好过被亲人疑心至此!”她说着,竟真的起身要去抓桌上的剪刀。沈砚心头一软,
下意识地扶住她。苏挽月是他亲手带大、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妹妹,
是他心中完美的侯府嫡女典范。看着她哭得肝肠寸断的模样,那点疑虑瞬间被心疼取代。
他暗叹自己多疑,竟被林晚照那副疯癫模样影响至此。“胡闹!”他低斥一声,
语气却已缓和,“大哥只是问问,没有不信你。起来吧。”苏挽月心下一松,
顺势柔弱地靠在沈砚臂弯里,抽噎着,眼底却飞快掠过一丝得意。然而,
这得意并未持续多久。当天傍晚,沈砚安排在暗处、负责监视我一举一动的暗卫头领沈忠,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书房,将一张墨迹未干的纸呈到沈砚案头。纸上,
清晰地画着苏挽月进入西厢小院的时间、动作,甚至包括她嘴角那一抹挑衅的冷笑。
簪匣如何被丢入炭盆,姨娘小像如何被举起砸落……一笔一划,如同冰冷的刻刀,
凿在沈砚心上。沈砚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猛地抬头看向沈忠,
眼神锐利如刀:“确凿?”沈忠面无表情,声音平板无波:“属下亲眼所见,分毫不差。
二**……未曾动手,亦未曾毁物。”沈砚沉默了许久。他挥了挥手,沈忠如影子般退下。
他独自坐在宽大的书案后,看着跳跃的烛火,
第一次对自己坚信了十多年的“真相”产生了巨大的动摇。他烦躁地揉着眉心,
最终将那张纸凑近烛火,看着它一点点化为灰烬。有些东西,一旦开始崩塌,
便再也无法复原如初。他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证据”。8我的日子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却像一潭死水,让我感到一种比疯人塔寒窟更深的窒息。在那里,
每天都有新的“考验”——疯癫病友的撕咬,看守太监的刁难,
王德海层出不穷的折磨手段……我需要时刻绷紧神经,在绝境中挣扎求生。
顾悬壶低沉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只要够狠,够疯,够让他们怕,
便没人能真正欺负得了你。晚照,你做得很好。”“但记住,出了塔,规矩就变了。
别人不动手,你便不能先亮刃!这叫‘理’字当头。占了理,占了先机,
便是天王老子也奈何你不得!”“可现在,他们不让‘坏人’来招惹我,我该怎么办?
”我的手指捻动着几根银针。那些被强行压制在心底的暴戾和破坏欲开始蠢蠢欲动。于是,
深夜,当侯府陷入沉睡,我悄无声息如同游荡的幽魂,
推开了苏挽月居住的、原本属于她的西厢小院的房门。苏挽月裹着锦被,睡得正沉,
丝毫未觉。我走到床边,静静地站着,缓缓抬起手,
袖中滑出一柄寒光凛冽、只有三寸长的精钢匕首。冰冷的刀锋在月色下反射出幽冷的光。
“你怎么……还不动手?”熟睡中的苏挽月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冰冷的威胁,
不安地蹙了蹙眉,翻了个身。我握紧匕首,手臂高高扬起,带着一股凌厉的决绝,
狠狠地朝着苏挽月枕边的位置刺了下去!“噗!
”锋利的匕首穿透了柔软的锦被和厚厚的床褥,深深钉入了下方的硬木床板!
巨大的震动和刺骨的杀意终于惊醒了苏挽月!“啊——!!!
”一声凄厉到极致的尖叫划破侯府寂静的夜空!苏挽月猛地弹坐起来,脸色惨白如鬼,
瞳孔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放大到极致!“鬼!鬼啊!救命!大哥!二哥!救救我!
”她连滚带爬地缩到床角,用被子死死裹住自己,抖得如同秋风中的枯叶,牙齿咯咯作响,
涕泪横流,整个人彻底崩溃。整个侯府瞬间被这声尖叫惊醒!
沈砚和沈墨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到了西厢院外,却被守夜婆子连滚爬爬地拦住。“侯爷!
二公子!去不得啊!”婆子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二**…二**她…梦游!
小说《疯人塔里爬出来后,我成了真千金》 疯人塔里爬出来后,我成了真千金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