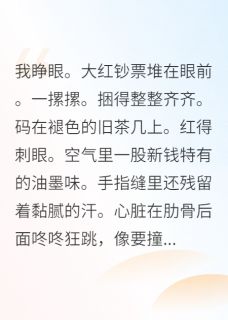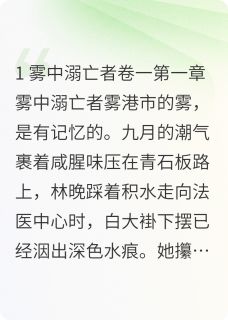明月御风的《重生后,我把彩礼捐给贫困山区》这部小说肯定可以让你喜欢,时而凝重时而搞笑,能看出明月御风是用心在写的。小说内容节选:”“放屁!”我妈尖叫起来,“你听谁嚼的舌根?鹏子多老实一孩子!我看你就是心野了!……
《重生后,我把彩礼捐给贫困山区》 重生后,我把彩礼捐给贫困山区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我睁眼。大红钞票堆在眼前。一摞摞。捆得整整齐齐。码在褪色的旧茶几上。红得刺眼。
空气里一股新钱特有的油墨味。手指缝里还残留着黏腻的汗。心脏在肋骨后面咚咚狂跳,
像要撞出来。这是我家。客厅。墙上挂钟指着下午两点。老式吊扇在头顶吱呀转,
扇叶上积了层灰。“清漪,发什么呆呢?”我妈的声音,带着压不住的喜气,
从厨房钻出来,“王鹏他妈刚走,这三十万,一分不少!点清楚了!人家可说了,
下个月初八是好日子,赶紧把证扯了!”王鹏。这两个字像烧红的针,猛地扎进我太阳穴。
疼。不是幻觉。我低头看自己的手。皮肤紧致,没有后来在流水线上熬出来的老茧和烫伤疤。
指甲缝是干净的。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领口有点松垮。我回来了。回到十年前。
回到王鹏他妈,把三十万彩礼现金,重重拍在我家茶几上的这一天。就是这堆钱,
把我推进了火坑。王鹏,他那张嘴,婚前甜言蜜语,婚后原形毕露。酗酒,堵伯,
输了钱就打我。婆婆刻薄,嫌我生不出儿子。我像个免费的保姆,出气筒,提款机。
三十万彩礼?早被王鹏赌光败光。我起早贪黑在厂里挣的那点血汗钱,也被他搜刮干净。
最后,为了躲他追到厂里的毒打,我慌不择路,
从夜班车间的铁楼梯上滚了下去……后脑勺磕在冰冷水泥地上的剧痛,似乎还在。“清漪?
听见没?赶紧把钱收你屋锁好!别放客厅招眼!”我妈端着盘切好的西瓜出来,
脸上笑开了花,仿佛这堆红票子是救命的仙丹。“王家条件多好,鹏子人也老实,
你嫁过去就等着享福吧!”享福?我胃里一阵翻搅。喉咙发紧。老实?是窝囊!
是披着人皮的豺狼!我看着那堆钱。崭新的。散发着诱人的,毁灭的气息。前世,
它买断了我的一生。买走了我的命。这一次,它得换个去处。“妈,”我开口,
声音有点哑,但异常平静,“这钱,不能收。”我妈脸上的笑瞬间冻住。西瓜盘差点脱手。
“你说什么疯话?!”“我说,这钱,不能要。”我重复,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王鹏,我不嫁。”“啪!”西瓜盘子被她重重顿在茶几上,几块鲜红的瓜瓤震落在地。
“阮清漪!你脑子被门夹了?!三十万!整整三十万!你爸累死累活一年才挣几个钱?
你弟眼看要上大学,哪不要钱?你不嫁?由得了你?!”她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
尖利的声音刺破午后的沉闷。“王家哪点配不上你?啊?人家有房!有车!鹏子工作也体面!
你一个高中毕业的,在破厂里打螺丝,能找到这样的,烧高香了!你还挑三拣四?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她越说越激动,胸口剧烈起伏,手指头快戳到我鼻尖。
门哐当一声被推开。我爸沉着脸进来,裤腿上还沾着泥点,显然是刚从地里被叫回来。
后面跟着我弟阮强,十八岁,一脸不耐烦地嚼着口香糖,眼睛却黏在那堆钱上。“吵吵什么?
大老远就听见!”我爸吼了一嗓子,目光扫过茶几上的钱,又落在我和我妈身上。“爸!
你管管她!”我妈立刻调转矛头,“你闺女出息了!三十万彩礼摆跟前,她说不要!
说不嫁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阮强吹了个泡泡,“啪”地破了。“姐,你傻啊?
三十万啊!够我买多少双**版球鞋了?你不嫁,我以后拿啥找媳妇?”我爸没立刻说话。
他摸出根廉价的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烟雾缭绕里,他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带着审视,
更多的是烦躁。“清漪,别胡闹。日子都看好了。王家……还行。嫁过去,安安稳稳的。
”“爸,”我看着他那张被生活压榨得沟壑纵横的脸,心里发酸,但语气更硬,
“王鹏不是好人。他赌钱,打人。这钱拿着,就是买我往火坑里跳。跳进去,就爬不出来了。
”“放屁!”我妈尖叫起来,“你听谁嚼的舌根?鹏子多老实一孩子!我看你就是心野了!
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没人。”我打断她,
目光扫过这一屋子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亲人”,心一点点冷下去。“我就是不想嫁。这钱,
谁爱要谁要。我明天就出去找活干,自己挣钱。”“你挣钱?你能挣几个钱?
厂里一个月撑死三千!”我妈气疯了,扑上来就要拧我胳膊,“我养你这么大,
是让你来气我的?这婚你不结也得结!钱必须收下!没商量!”我侧身躲开她的手。“钱,
我不会收。”我盯着她,一字一顿。“明天天亮前,我会把它处理掉。”“你敢!
”我妈目眦欲裂。“你看我敢不敢。”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
把他们的怒骂、威胁、阮强阴阳怪气的嘲讽,通通关在了卧室门外。背靠着冰凉的门板,
我大口喘气。手心里全是冷汗。处理掉?怎么处理?一个念头,像黑暗中擦亮的火柴,
猛地跳了出来。——捐了。捐给真正需要的人。前世模糊的记忆碎片浮现。
好像是在某个疲惫不堪的深夜,刷手机时,瞥见过一个关于西南边远山区极度贫困的报道。
那里缺水缺电,孩子们在四面漏风的“教室”里上课,铅笔短得捏不住……当时麻木的心,
似乎也微微刺痛了一下。就是它了。我扑到床边,
从枕头底下摸出那部屏幕碎了个角的旧手机。手指因为激动和紧张微微发抖。网络很慢。
我输入关键词,一遍遍刷新。找到了!一个扎根当地多年的公益助学机构。网页很简陋,
但信息透明。照片上,孩子们穿着不合身的破旧衣服,小脸脏兮兮的,眼睛却亮得像星星。
他们身后,是摇摇欲坠的土坯房教室。页面最下方,有详细的捐款账户信息。公对公账户,
接受社会监督。就是这里。心跳如擂鼓。一个疯狂又无比清晰的计划在脑中成型。我起身,
把耳朵贴在门上。客厅里的吵闹声小了些,变成压抑的争执和咒骂。
隐约听见我爸在吼“锁好钱!别让她发疯!”他们防着我。我轻轻走到窗边。
老式的铁栅栏窗。外面是窄窄的巷子。天快黑了。时间紧迫。必须今晚行动。
我翻出自己唯一的一个旧双肩包,抖掉里面的杂物。很小,装不下多少。只能分次拿。
夜深了。客厅的灯终于灭了。我爸沉重的鼾声隔着门板传来。我妈大概也骂累了。
我屏住呼吸,像幽灵一样,赤着脚,悄无声息地拧开房门。客厅一片漆黑。
只有窗外一点惨淡的月光透进来,勉强勾勒出家具的轮廓。那堆钱,还放在茶几上。
被一块我妈盖电视机用的旧绒布,潦草地盖着。我蹑手蹑脚走过去。心脏跳得快要炸开。
手心全是汗。轻轻掀开绒布一角。红艳艳的钞票在微弱的光线下,依旧扎眼。我抓了一把。
很厚。塞进双肩包。再抓一把。再塞。包很快鼓胀起来,拉链勉强拉上。沉甸甸的。
压得肩膀生疼。这不是钱。这是枷锁。是毒药。我背上包,小心翼翼地挪到大门边。
老旧的铁门,开锁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浑身僵硬,
竖着耳朵听。鼾声依旧。轻轻拉开门缝。闪身出去。再轻轻带上。
冰冷的夜空气猛地灌入肺里。我打了个寒噤,拔腿就跑。拖鞋拍打在坑洼的水泥地上,
发出急促的“啪嗒”声,在空旷的小巷里回荡。一口气跑到两条街外的自助银行。
24小时营业。玻璃门感应打开。里面空无一人。惨白的灯光照得人脸发青。
我把鼓囊囊的双肩包卸下来,放在冰冷的ATM机台面上。手抖得厉害,
试了几次才把银行卡**去。输入密码。屏幕亮起。选择“无卡存款”。我拉开背包拉链,
把那捆捆扎眼的红色钞票,一股脑塞进存款口。机器发出嗡嗡的读钞声。一捆。两捆。
三捆……屏幕上数字飞快跳动。存款成功。机器吐出凭条。我抓起凭条,
看都没看上面的数字,胡乱塞进口袋。背上瞬间轻了的包,转身就走。心跳依然很快,
但不再是恐惧。一种奇异的、挣脱束缚的轻松感,混合着干坏事的紧张**,冲刷着我。
回家。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轻手轻脚。打开卧室门,溜进去,反锁。第一包,成功。客厅里,
钱山矮下去一小截。没人发现。后半夜。我如法炮制。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出门,
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次听到鼾声,都像得到赦免。
每一次把那些滚烫的钞票塞进冰冷的机器,都像是扔掉一块烧红的烙铁。天快蒙蒙亮时,
我背回了空荡荡的双肩包。最后一次。茶几上,只剩下盖钱的那块旧绒布,皱巴巴地摊着,
下面空空如也。三十万。没了。我瘫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后背靠着床沿。
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指尖冰凉。但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
极度紧张后的虚脱感袭来。我闭上眼。不管了。天塌下来,也等睡醒再说。这一觉,
睡得昏天黑地。是被震耳欲聋的砸门声和歇斯底里的尖叫惊醒的。“阮清漪!你给我滚出来!
钱呢?!我的钱呢?!”是我妈。声音尖利得变了调,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紧接着是阮强的怒吼:“姐!**把彩礼钱弄哪去了?!快开门!”门板被砸得砰砰作响,
灰尘簌簌往下掉。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开。我坐起身。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窗外天光大亮。
该来的,总会来。我慢吞吞地穿好衣服,走过去,拧开了反锁。门刚开一条缝,
我妈就疯了似的撞进来,差点把我带倒。她眼睛赤红,像要吃人,直扑向客厅。“钱!
我的钱!”她一把掀开茶几上那块孤零零的绒布,下面空空荡荡。“啊——!
”她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猛地转身,手指颤抖地指着我,“钱呢?!阮清漪!
你把钱藏哪了?!拿出来!快拿出来!”阮强也冲了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钱呢?!是不是你偷拿出去花了?!说啊!
”我爸铁青着脸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根赶鸡用的竹竿,胸口剧烈起伏,死死瞪着我,那眼神,
像在看一个仇人。“钱,”我掰开阮强的手,理了理被揪皱的领子,声音异常平静,
甚至带着一丝解脱,“没了。”“没了?!”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冲上来就要撕打我,
“什么叫没了?!三十万!那是我的命!你把它弄哪去了?!是不是给野男人了?!
”我侧身躲开她的爪子。“捐了。”两个字。像两颗冰雹砸进滚油锅。客厅里瞬间死寂。
三双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我。仿佛我在说什么天方夜谭。“捐……捐了?
”阮强第一个反应过来,像听到了全世界最荒谬的笑话,嗤笑出声,“姐,你睡糊涂了吧?
捐给谁?慈善机构?你当你是什么大善人?别他妈逗了!”“对。”我拿出手机,
点开昨晚保存的捐款记录截图,还有那个公益机构的简陋页面,屏幕转向他们,
“西南山区助学基金。三十万。昨晚捐的。有电子回执。”手机屏幕不大。
但那醒目的捐款金额数字“300,000.00”,和下方那个陌生的公益机构名称,
像烧红的烙铁,烫进了他们的眼睛。我妈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
她死死盯着屏幕,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突然,她像被抽掉了骨头,
整个人软绵绵地向后倒去。“妈!”阮强惊呼,赶紧扶住她。
我爸手里的竹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踉跄一步,扶住门框,才没摔倒。
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瞬间灰败下去,像是老了十岁。他看着我,眼神空洞,
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女儿。“你……你……”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声,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阮清漪!你这个疯子!败家子!丧门星!”阮强扶着我妈,
扭头对我破口大骂,额头上青筋暴跳,“那是我的钱!我的房子!我的车!你凭什么捐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他松开我妈,像头发狂的野兽朝我扑过来。
我爸猛地回神,一把死死抱住暴怒的阮强。“强子!别动手!”“爸!她毁了咱家!
她毁了我!”阮强拼命挣扎,嘶吼着,眼睛通红。我妈瘫在椅子上,终于缓过一口气,
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嚎:“我的老天爷啊!造孽啊!我怎么生了这么个讨债鬼啊!
三十万啊!那是王家的钱啊!你让我们拿什么赔给人家啊!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
呜呜呜……”哭声,骂声,吼叫声,混杂着阮强徒劳的挣扎和我爸沉重的喘息,
几乎要把这小小的客厅掀翻。我站在那里。像风暴中心唯一静止的点。
看着他们的崩溃、愤怒、绝望。心里没有想象中的快意,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前世,
为了这三十万,我赔上了一生。他们,又何尝不是推我进火坑的帮凶?现在,枷锁没了。
火坑,谁爱跳谁跳。“王家那边,”我提高声音,压过屋里的混乱,“你们自己去解释。
钱,是我捐的。人,我不会嫁。”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任何一个人,
转身走进自己那间狭小的卧室,开始收拾东西。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服。几本旧书。
身份证。还有那张余额只剩下几百块的银行卡。一个旧行李箱就装完了。
客厅里的哭嚎咒骂还在继续。“你要去哪?!你个没良心的!你给我站住!
”我妈尖叫着要扑过来拦我。我爸死死拽着她,也拦着又想冲过来的阮强。
他看着我拖着行李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愤怒,有绝望,
似乎还有一丝极淡的、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茫然。“让她滚!”阮强嘶吼,
“滚了就永远别回来!我没你这个姐!”我拖着箱子,目不斜视地从这一片狼藉中走过,
拉开大门。清晨带着凉意的空气涌进来。“爸,妈,”我停在门口,没有回头,“保重。
”身后是更尖锐的哭骂和诅咒。我关上门。把那令人窒息的绝望和愤怒,彻底隔绝。
拖着箱子走在清晨冷清的街道上。阳光有些刺眼。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早点摊飘来的烟火气。自由的味道。手机在口袋里疯狂震动。掏出来一看,
屏幕上跳动着“王鹏”两个字。我直接挂断。拉黑。世界,清静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王家不会善罢甘休。家里那摊烂账,也还没完。但我脚步没停。先去银行,
把卡里仅剩的几百块取出来。然后直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邻市的长途车票。那里工厂多,
机会多。消费也低。坐在颠簸的大巴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手机又响了。
是个陌生本地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通。“阮清漪?!”是王鹏他妈那尖利刻薄的声音,
隔着听筒都能感觉到那股咬牙切齿的恨意,“你什么意思?!彩礼钱呢?!你敢耍我们王家?
!你妈说你把钱捐了?!你放屁!赶紧给我还回来!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钱捐给山区孩子上学了。有凭证。退不了。”我语气平淡,“至于我跟你儿子,
婚约作废。你们另找高明吧。”“作废?!你说作废就作废?!
”王鹏他妈气得声音都劈了,“你当我们王家好欺负?!我告诉你阮清漪!这事没完!
你不把钱吐出来,不乖乖嫁过来,我让你全家在本地混不下去!我……”我直接挂了电话。
拉黑这个号码。世界再次清静。靠着车窗,疲惫感排山倒海般袭来。我闭上眼。我知道,
这只是第一波风浪。落脚的地方是个城中村。鱼龙混杂,房租便宜。
我租了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单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公用厕所和水房在走廊尽头。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是找工作。前世在电子厂做过,熟手。
很快就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厂里找到了流水线普工的活。白班夜班轮换,计件工资。累,
但工资能按时发。日子像上了发条。车间、食堂、出租屋。三点一线。手机很安静。
家里没再联系我。大概是真的恨毒了,或者忙着应付王家的怒火。
王鹏倒是换过几个号码打来,歇斯底里地咒骂、威胁,甚至哀求,说他妈气得住院了,
说只要我回去,钱的事可以商量。我每次都平静地听完,然后拉黑。商量?回去?绝无可能。
流水线的日子枯燥得像砂纸,磨得人麻木。但心里是踏实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
干净。偶尔下班早,会去城中村口的小网吧。一块五一个小时。不是为了玩,
是想看看那个公益机构的网页。没有更新。捐款公示栏里,
“阮女士”和那串醒目的“300,000.00”排在最新一行的首位。看着那串数字,
心里会泛起一丝奇异的暖流。像冰冷的石头缝里,渗出了一点温热的泉水。这钱,没白扔。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一个普通的夜班结束。凌晨四点,天还黑着。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
走在回出租屋的冷清街道上。快到巷子口时,路灯昏暗的光线下,
一个人影猛地从阴影里蹿出来,拦在我面前。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后退一步,攥紧了包带。
是王鹏。他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
浑身散发着浓重的烟味和……酒气。眼睛死死盯着我,里面布满了红血丝,
像濒临疯狂的野兽。“清漪……”他声音嘶哑,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哀求和怨毒,
“我总算找到你了!”我全身的神经瞬间绷紧。环顾四周。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
只有远处偶尔驶过的车灯。“你想干什么?”我冷声问,脚步悄悄往后挪,
寻找逃跑或者呼救的机会。“钱……”他往前逼近一步,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那三十万……我妈真的气病了!住院费都欠着了!算我求你了!你把钱还回来!
哪怕……哪怕先还一半也行!不然我们家真的完了!”“我说过了,钱捐了。退不了。
”我盯着他,防备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捐了?!你骗鬼呢!”王鹏突然暴怒起来,
脸上的哀求瞬间被狰狞取代,“那么多钱!你说捐就捐?谁信?!阮清漪!你别给脸不要脸!
是不是在外面傍上大款了?把钱贴给野男人了?!啊?!”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横飞,
伸手就来抓我胳膊。“跟我回去!今天你不把钱吐出来,别想走!”我早有防备,
猛地往后一躲,他的手抓了个空。“王鹏!你再动手我喊人了!”我厉声警告,心脏狂跳。
“喊人?你喊啊!”他像是彻底撕破了脸,狞笑着再次扑上来,“我看谁敢管闲事!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个扫把星!**!今天不把钱拿出来,我弄死你!”他力气很大,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另一只手扬起,作势要打。恐惧瞬间攫住了我。
前世被他殴打的剧痛记忆,排山倒海般涌来。不能!绝不能再挨打!求生的本能爆发。
我猛地低头,狠狠一口咬在他抓着我手腕的那只手上!“啊——!
”王鹏发出一声痛极的惨叫,触电般松开了手。趁他吃痛捂手的瞬间,我转身就跑!
用尽全身力气,朝着不远处有24小时便利店灯光的方向狂奔!“阮清漪!你站住!
你给我回来!”王鹏在身后咆哮着追来。夜风呼呼刮过耳边。肺部**辣地疼。
高跟鞋(厂里要求穿工鞋,下班才换的旧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我根本不敢回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到人多的地方!便利店越来越近!
明亮的灯光就在眼前!“救命!抢劫!救命啊!”我用尽力气嘶喊起来。便利店门口,
小说《重生后,我把彩礼捐给贫困山区》 重生后,我把彩礼捐给贫困山区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