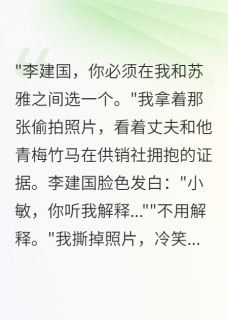最新小说《风絮》,主角是阿絮阮素心萧彻,由今时懿创作。这本小说整体结构设计精巧,心理描写细腻到位,逻辑感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让人痛快淋漓。非常值得推荐!哪里还有半分帝王威严?那血腥的物件和刺鼻的气味,瞬间勾起我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眼前仿佛又闪过凤仪殿的大火和白玉阶上的鲜血……
《风絮》 风絮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
他曾说我是他心尖上的明月,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后来,
他亲手将我碾入尘埃,只为护住他心口那粒灼人的朱砂痣。五年后,我携新夫回京赴宴,
他竟当众跪在我染尘的裙边,双目赤红地哀求:“朕愿舍弃江山,为赘婿,
只求你回头看一眼!”我垂眸,指尖拂过他颤抖的龙袍衣袖,
声音轻得像御花园里最后一片落樱:“陛下,迟来的深情,比那御沟里的腐草还要轻贱。
”车轮碾过朱雀门外的青石板路,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声响,一下下,
仿佛敲在心上最陈旧的伤疤上。正是暮春时节,御街两侧的垂柳,
不知疲倦地抛洒着漫天飞絮,细白如雪,轻柔似羽,却带着一种无孔不入的侵略性。
几缕柳絮调皮地钻过未曾关严的车帘缝隙,拂过我的鼻尖。“咳……”我下意识掩唇,
喉间泛起一丝熟悉的痒意。身侧,一只骨节分明、带着薄茧的手伸了过来,
带着清浅的药草气息,稳稳地将窗缝合拢,隔绝了外面喧嚣的人声和恼人的飞絮。
温润的嗓音随之响起,熨帖地拂过耳畔:“是知恒疏忽了,忘了夫人畏絮。
”沈知恒将一只小巧的紫铜暖炉塞进我的掌心,炉壁温热,恰到好处地驱散了指尖的微凉,
“前方便是朱雀门了。”我握紧暖炉,指尖感受着那沉稳的暖意,
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帘外。故国都城的气息,
混杂着泥土、车马、脂粉和某种深植于记忆深处的宫廷熏香,汹涌地扑了进来。
这气息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捅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布满血污的门。五年前,
也是这样的暮春,柳絮漫天飞舞,如同天地间一场悲凉的雪祭。
我被两个面无表情的粗壮太监,像拖拽一袋破败的垃圾,粗暴地从凤仪殿一路拖出宫门。
冷汗浸透了单薄的中衣,黏腻地贴在皮肤上,而那些轻盈的柳絮,
却无孔不入地钻进衣领、袖口,甚至粘附在汗湿的鬓角,
带来一种令人作呕的、被无数细小蛆虫啃噬的错觉。彼时,我那尊贵的夫君,大梁天子萧彻,
正拥着他心尖上的那粒朱砂痣——新晋的贵妃阮素心,高高地立在巍峨的宫城楼头。
他俯视着下方狼狈不堪的我,眼神冷漠得像在看一只即将被碾死的蝼蚁。
阮素心依偎在他怀里,唇角勾起一抹胜利者般娇媚又残忍的弧度,那姿态,
深深地烙印在我屈辱的眼底。“怕么?”沈知恒温厚的手掌忽然覆上我微微颤抖的手指。
他的掌心有着常年采药、研磨药材留下的薄茧,触感微糙,却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踏实感。
这与萧彻那双因常年握剑持弓而布满硬茧、充满力量却也曾带给我无尽冰冷的手,截然不同。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口翻涌的寒意和那几乎要冲破喉咙的旧日腥甜,缓缓摇头,
唇边甚至努力勾起一丝极淡的笑意:“不过是些旧日尘埃化成的蝶,风一吹便散了。
有何可怕?”话音未落,行驶的马车猛地一顿,停了下来。
帘外原本嘈杂的人声瞬间被一种肃杀的寂静取代。紧接着,是整齐划一的兵甲摩擦之声。
一只骨节分明、却透着不容置疑威压的手,猛地掀开了车帘!
金线绣龙的玄色衣摆带着帝王独有的冷冽气息扫过青砖地面。
萧彻那张我曾刻骨铭心描摹过的脸,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五年时光,
并未在他脸上留下多少风霜,反而沉淀出一种更深沉的帝王威严,只是此刻,
那双曾盛满星辰大海、也曾对我凝满深情的凤眸里,此刻翻涌着令人心惊的猩红血丝,
仿佛濒临疯狂的野兽。他的目光死死地钉在我脸上,仿佛要将我整个人吸进去。
“阿絮……”他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声音干涩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
饱含着难以置信的痛楚和一种濒临崩溃的执念。然而,当他的视线下移,
落在我与沈知恒依旧交握的双手上时,那翻涌的猩红瞬间凝固,
随即爆发出一种被最滚烫的烙铁灼伤的剧痛。他竟踉跄着后退了一步,
撞在身后的御前侍卫身上,脸色瞬间惨白如金纸,仿佛那交握的双手,是世间最致命的毒药。
五年前,我苏絮,也曾是萧彻捧在手心、视若珍宝的明月。我是镇国大将军苏震的独女,
自幼习武,性情爽朗。那年皇家围猎,叛军突起,流矢如雨。混乱中,
一个幼小的身影因惊马而即将被践踏。千钧一发之际,我飞身扑救,将孩子护在身下,
一支淬毒的冷箭却穿透了我的胸膛,离心脏只差分毫。剧痛与黑暗吞噬意识前,
我看到萧彻惊恐万状地向我奔来,那眼神里的恐惧和心疼,
曾是我在生死边缘抓住的唯一浮木。他衣不解带地守在我床前,亲手为我换药,喂我汤水,
一遍遍在我耳边低语:“阿絮,你是朕的命,是朕心尖上的明月,没有你,
朕的江山都是灰暗的。”他握着我的手,将那支定情的鸾凤剑放在我枕边,“以此剑为誓,
此生唯你,绝不负卿。”那时的誓言,滚烫真挚,烙印在我心上。
我凭着过人的意志和御医的全力救治活了下来,那道狰狞的疤痕却永远留在了心口。
萧彻力排众议,立我为后。起初的岁月,如蜜里调油。他会在早朝后匆匆赶回凤仪殿,
只为陪我吃一碗新熬的莲子羹;会在御花园为我栽满我喜爱的木芙蓉;会在夜深人静时,
一遍遍描摹我眉眼的轮廓,说我比明月更清辉。凤仪殿的每一个角落,
都曾浸满我们的浓情蜜意。直到阮素心的出现。她是户部尚书阮正明的嫡女,
据说在萧彻还是不受宠的皇子时,曾对他有过一饭之恩。她柔弱、美丽,
像一朵精心培育的菟丝花,眉眼间……竟与我有三分相似。起初,萧彻只是感念旧恩,
对她多加照拂。但渐渐地,他停留在她宫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会在听她弹奏琵琶时,
露出我许久未见过的、放松而沉醉的笑意;会在她蹙眉轻咳时,
流露出我几乎要遗忘的紧张和心疼。宫中开始有流言蜚语,说阮贵妃才是陛下心头的朱砂痣,
而我这个皇后,不过是因为挡箭有功,又恰巧有几分像她,才得了这凤位。我起初不信,
直到那晚,我亲眼看见在御花园的假山后,阮素心踮起脚尖,吻上了萧彻的唇。而他,
没有推开。质问换来的是他第一次对我发怒:“阿絮!你何时变得如此善妒?素心她身子弱,
心思单纯,不过是感念朕的恩情!你身为皇后,要有容人之量!”那“容人之量”四个字,
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我心窝。阮素心的手段远比我想象的阴毒。
她先是利用一只精心**的猫,“无意”抓伤了前来送赏赐的、德高望重的老太后。
太后震怒,萧彻却只轻描淡写地斥责了那猫两句,
转头便赏了阮素心一串价值连城的南海珍珠压惊。老太后气得一病不起,不久便薨逝。
这成了压垮骆驼的第一根稻草,也让萧彻对我这个“未能尽孝”的皇后,心生芥蒂。
真正的致命一击很快到来。阮素心宫中“发现”了写着太后生辰八字、扎满银针的巫蛊人偶。
所有证据,都隐隐指向凤仪殿。我百口莫辩。萧彻震怒,那双曾盛满柔情的眼睛,
此刻只剩下冰冷的怀疑和帝王不容置疑的威严。他下令彻查。那日,凤仪殿的总管太监,
那个曾对我忠心耿耿、看着我长大的福公公,被阮素心宫里的太监总管王德海押着,
颤巍巍地端着一杯鸩酒来到我面前。王德海腕上赫然三道新鲜的血痕,皮肉外翻,
他阴恻恻地说:“皇后娘娘,陛下口谕:您……只是替身。如今正主归位,您该让路了。
这杯酒,是贵妃娘娘赏您的体面。”铜镜里,映出不知何时悄然潜入的阮素心。
她穿着云霞般绚烂的宫装,头上珠翠环绕,比我这正宫皇后还要华丽三分。
她拔下我发间那支象征着皇后身份的九尾凤钗,放在手中把玩,朱唇贴近我的耳朵,
声音带着胜利者的甜腻和刻骨的恶意:“姐姐,陛下说,当年叛军势大,
娶你不过是权宜之计,好让我这真正的‘明月’避开锋芒,安全无虞。如今叛党早已伏诛,
阮家也位极人臣,你这赝品,自然该让位了。你看,
连你为陛下挡的那一箭……他原是要替我受的呢。”她冰凉的指尖,带着尖锐的护甲,
狠狠戳在我心口那道狰狞的疤痕上,“你抢了我的机缘,活该受这些苦!
”凤仪殿燃起熊熊大火的那一夜,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火势来得蹊跷而猛烈。
我被浓烟呛醒时,殿门已被反锁。我拖着被大火燎伤、又被掉落的梁木砸伤的腿,
用尽全身力气撞开窗户,滚落在冰冷的地上。身后是吞噬一切的烈焰,
身前是长长的、通往他寝宫的三百级白玉石阶。膝盖碎裂般的剧痛,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鲜血从破碎的裙摆下渗出,在身后蜿蜒成一条刺目的血河。
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见他!我要问问他,这五年情爱,难道都是虚妄?这皇后之位,
难道真是替他人做嫁衣裳?我拖着残腿,在宫人惊恐或漠然的目光中,
爬过一级又一级冰冷的石阶。指甲在光滑的石面上抠出血痕,汗水、血水和泪水混在一起,
模糊了视线。终于爬到他的寝宫外,却听见里面传来阮素心娇柔婉转的琵琶声,
和他低沉的、带着宠溺的笑语。“陛下,皇后娘娘她……”内侍战战兢兢地通报。
琵琶声戛然而止。宫门打开,萧彻搂着只披着薄纱、我见犹怜的阮素心走了出来。
月光清冷地洒在他明黄的龙袍上,也照亮了我此刻的狼狈:发髻散乱,满脸血污,衣裙褴褛,
染血的膝盖在石阶上留下触目惊心的痕迹。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心疼,
只有被打扰的不悦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皇后?”他蹙眉,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的、肮脏的乞丐,“如此失仪,成何体统?惊扰了贵妃,你担待得起吗?
来人,送皇后回宫!禁足三月,好好反省!”他甚至没有问一句我为何如此模样,
没有看一眼我身后的血路。他怀中的阮素心,将脸埋在他胸口,肩膀微微耸动,似乎在哭泣,
但我分明看到她嘴角勾起的那抹得意。那一刻,心口的箭疤,连同那颗曾为他炽热跳动的心,
彻底死了。冰冷刺骨,比这玉阶的寒意更甚万倍。后来,是沈老将军(父亲旧部)拼死闯宫,
以告老还乡为代价,加上我自请废后,才从萧彻手中换得一块出宫令牌。离京那日,
天色阴沉。阮素心盛装出现在城门口,美其名曰“送别旧主”。她屏退左右,
走到我的破旧马车前,声音带着施舍般的怜悯和刻毒的炫耀:“姐姐,走得远些吧。
陛下昨夜还对我说,看到你这张脸,就想起他不得已的隐忍岁月,着实令人不快呢。
”她顿了顿,笑容愈发灿烂,“哦,对了,忘了告诉你,那支射中你的毒箭……是我安排的。
本想除掉你这个碍眼的赝品,没想到你命大,还让陛下对你生了那么久的愧疚。不过,
现在都不重要了。”马车驶离京城,我将那块象征废后的令牌狠狠扔出窗外。
身后是囚禁了我五年青春与真心的牢笼,前方是茫茫未知的深渊。离宫后的日子,
是从云端坠入泥泞。身体上的伤痛(腿伤、心口旧伤复发)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
几乎将我彻底摧毁。父亲旧部的接济有限,且为了避嫌不能公开。我隐姓埋名,
带着贴身侍女阿蛮(一个忠心耿耿的武婢),颠沛流离。心口的箭伤在阴雨天总是隐隐作痛,
如同心魔的提醒;腿伤更是留下了病根,每逢寒冷便钻心地疼,走路也微微跛足。
昔日的皇后光辉荡然无存,
我只是一个面容憔悴、身有残疾、需要靠典当仅存的首饰和替人缝补浆洗度日的妇人。
世态炎凉,白眼和欺凌是家常便饭。最黑暗的一次,是在一个偏僻小镇,
几个地痞觊觎阿蛮的美貌和我们仅剩的盘缠。阿蛮虽武艺高强,却双拳难敌四手,
我也因腿伤行动不便。危急关头,一个背着药篓、风尘仆仆的青衫男子出现。他身手敏捷,
几根银针精准地刺入地痞的穴位,瞬间让他们瘫软在地。他便是沈知恒。
他没有多问我们的来历,只是默默帮我们解了围,又仔细查看了我的腿伤和苍白的面色。
“夫人这腿伤,拖得太久,寒气已深入骨髓。心脉亦有旧损,郁结于心,需徐徐图之。
”他的声音温和而笃定,带着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起初,我对他充满了警惕,
拒绝了他的诊治。但他并未放弃,只是在不远处摆了个义诊的摊子。阿蛮打听回来,
说他是游历四方的名医,人称“玉面圣手”,医术高明,
尤其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和调理沉疴旧疾,且心地仁善,常免费为穷人治病。渐渐地,
我放下些许心防,默许他为我施针用药。他的医术确实高明。几剂温补驱寒的汤药下去,
腿上的刺痛竟真的缓解了许多。他施针的手法极稳极准,银针落下,带着一种奇特的温热感,
缓缓驱散着体内的寒气。他从不问我的过往,只专注眼前病痛。偶尔闲聊,
也只谈些山川风物、草药习性。他的眼神清澈平和,没有怜悯,没有探究,
只有医者仁心的专注和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一次施针后,我心口旧伤突然剧痛,
冷汗瞬间湿透衣衫。沈知恒脸色一变,迅速取出一枚金针,刺入我胸前几处大穴。
剧痛如潮水般退去,我虚脱地靠在榻上。他沉默地收回针,
良久才低声道:“夫人这心脉之伤,凶险异常,当年能活下来,已是万幸。只是这郁结之气,
若不疏解,终成大患。”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眼中看到如此深重的忧虑,
不是为了他的医术名声,而是真切地为了我这个人。在他的精心调理和无声的陪伴下,
我的身体一点点好转,腿脚虽不能恢复如初,但行走已无大碍,
心口的疼痛也发作得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他用他如春风化雨般的温和与尊重,
一点点融化了我心头的坚冰,抚平了我灵魂深处的创伤。他带我去山间采药,教我辨认草药,
告诉我每一种花草的生命力;他会在雨夜为我守一盏灯,
诵读些闲散的医书游记;他会在我因噩梦惊醒时,及时递上一碗温热的安神汤。不知不觉间,
依赖悄然滋生。五年时光,在江南小镇的潺潺流水和草药清香中静静流淌。
沈知恒用他的方式,为我重建了一个安稳的世界。他向我提亲的那日,阳光正好,
院子里他亲手栽种的药圃生机盎然。他握着我的手,眼神真挚而温暖:“沈某身无长物,
唯有这一身医术和一颗真心。夫人若不嫌弃,余生,知恒愿为夫人调理身心,遮风挡雨,
不离不弃。”没有华丽的誓言,却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让我心安。我看着他清俊的眉眼,
缓缓点头,将冰冷了多年的手,交到了他温热的掌心。此次回京,
是沈知恒接到了太医院的特别征召。江南突发时疫,他研究出的药方成效卓著,
京中权贵亦有染疾者,故特邀他入京会诊。我本不愿回来,但知恒说,有些心结,
终究需要面对才能彻底放下。他握着我的手说:“夫人,有我在。”宫宴设在琼华殿,
灯火辉煌,丝竹悦耳。我与沈知恒坐在下首靠前的位置,并不显眼,
却足以让御座上的那个人看清。萧彻的目光,从我们踏入殿门的那一刻起,
就像淬了毒的钩子,死死地钉在我身上,
带着狂喜、难以置信、痛苦和一种近乎癫狂的占有欲。五年时光,
并未在我身上留下太多沧桑的痕迹,反而在沈知恒的精心调养下,褪去了宫中的苍白和紧绷,
多了几分江南水乡滋养出的温润平和。只是那双眼眸深处,沉淀着挥之不去的疏离和冷意。
宴至中酣,气氛正浓。萧彻突然摔了手中的九龙玉杯!清脆的碎裂声如同惊雷,
震得满殿歌舞骤停,鸦雀无声。他猛地站起身,赤红着双目,手指颤抖地指向沈知恒,
声音因激动而嘶哑变形:“你!一个江湖郎中!乡野匹夫!也配娶朕的皇后?!
也配坐在朕的琼华殿上?!”满殿死寂,落针可闻。王公大臣们噤若寒蝉,
女眷们吓得花容失色。沈知恒神色不变,只是微微侧身,将我更严密地挡在他身后,
目光平静地迎向帝王的怒火。萧彻却已踉踉跄跄地冲下御阶,玄色的龙袍下摆拖曳在地。
他完全不顾帝王威仪,像一个输光了所有的赌徒,直直冲到我面前。
在百官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竟然“噗通”一声,
直挺挺地跪倒在我染着些许宫道尘埃的裙摆边!“阿絮!阿絮!”他仰着头,
双手死死抓住我的裙角,像溺水之人抓住最后的浮木,声音破碎而绝望,“朕错了!
朕真的错了!你回来!你看!你看朕替你报仇了!”他语无伦次,
竟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明黄色的、却沾染着大片暗褐色污迹的帕子,
颤抖着手打开——里面赫然裹着几缕乌黑的、粘连着些许暗红皮肉的发丝!
浓重的血腥气瞬间弥漫开来!“是阮素心那个**!她是北狄派来的细作!是她害了太后!
是她害了你!朕把她凌迟了!千刀万剐!你看!这是她的头发!她的皮肉!朕替你报仇了!
阿絮!你看看!你原谅朕!跟朕回去!朕废六宫!朕不要这江山了!朕愿为赘婿!
只求你回头!只求你再看看朕!”他歇斯底里地喊着,涕泪横流,状若疯魔,
哪里还有半分帝王威严?那血腥的物件和刺鼻的气味,瞬间勾起我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
眼前仿佛又闪过凤仪殿的大火和白玉阶上的鲜血。我脸色煞白,身体晃了晃。
“内子闻不得血气,亦受不得惊扰。陛下厚爱,恕难承受。容臣告退。
”沈知恒的声音沉稳有力,如同定海神针。他一手稳稳扶住我几乎要软倒的身体,
另一手看似随意地拂过,一股清冽的药草气息瞬间冲散了那令人作呕的血腥。
他不再看跪在地上的帝王,揽着我,转身便走。他的臂膀坚实有力,
隔绝了身后那混乱、疯狂和无数道震惊、探究的目光。萧彻如何肯罢休?
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嘶吼着追了出来。宫道幽深,夜风凛冽,
吹散了他披散的头发和破碎的呼喊:“阿絮!你回来!你从前最爱朕的!你忘了吗?!
那年围猎遇刺,你扑上来替朕挡箭!你说过!你说此生只爱朕一人!至死不渝!你不能食言!
阿絮——!”那一声声绝望的呼唤,撕扯着旧日的疮疤。我猛地停住脚步,
在沈知恒的搀扶下,缓缓转过身。檐下悬挂的宫灯,将我们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也将我脸上冰冷的泪痕照得无所遁形。“陛下,”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风声,
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冰冷,“您记错了。”萧彻的嘶吼戛然而止,他僵在原地,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那年围猎遇刺,”我抬手指向远方,仿佛穿透了时光,“臣女扑救的,
是陛下您身后,那个因惊马即将被踏成肉泥的无辜孩童。”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冷的刀,
剜开他记忆的伪装,“至于挡箭……”我的手,缓缓抚上心口,隔着衣料,
似乎也能感受到那道狰狞凸起的疤痕传来的悸痛,“这一箭穿胸而过时,陛下您,
正紧紧抱着吓晕过去的阮贵妃,对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臣女,厉声呵斥——‘滚开!
休要惊扰圣驾!’”夜风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萧彻僵硬的龙袍上。他如遭雷击,
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只能徒劳地瞪大眼睛,
看着我如同看一个来自地狱的、控诉他罪孽的幽灵。那些被他刻意遗忘、扭曲的真相,
被我最平静也最残忍的话语,血淋淋地撕开,摊在清冷的月光下。宫宴风波后,
小说《风絮》 风絮精选章节 试读结束。